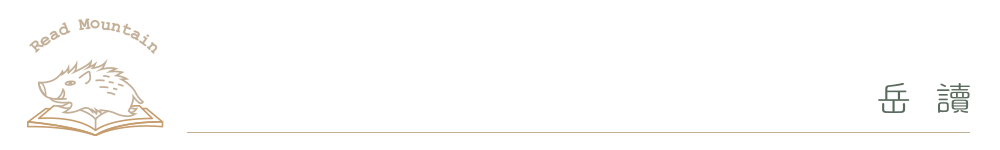幾年前我參與了一趟橫斷中央山脈的行旅,穿過台灣的心臟地帶,從島嶼西緣一逕走到島嶼東側,南投地利村入山,再踏上平地時,已是花蓮富源村,整整十日,踏的是毫無人蹤的荒徑:丹大西溪、堪姆卒山、關門西稜、馬太鞍溪、倫太文山,我們走的路被稱為台灣的最後祕境,路基早已消逝而必須自己披荊斬棘於廣漠山稜中找路開路的關門古道。
那一團夥伴中,有五位布農族族人,攜著後膛制式獵槍。我們一路踉蹌跌撞,上攀三千公尺,寒霜暴雨走在台灣屋脊上,風障霧暝穿梭迷茫森林裡。五位裡頭有一對夫妻,行至半途,我才知道原來這趟冒險的山行被Lizu 與Ali 當作他們的蜜月旅行。
Lizu 是布農卡社群人,Ali 是布農丹社群人。一九三三年,日本人實施集團移住,Ali 所屬的丹社Manqoqo 家族被迫遷移到中央山脈兩側,一半定居地利,一半移住富源。新婚的他們,想要橫越中央山脈到花蓮去探訪Manqoqo 家族的親戚,我們走的路,就是他們祖先在日本殖民主壓迫下被迫遷移的流亡路。
一路上,餐風露宿,彼此同甘共苦。那場旅程回來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幾個月後,某次閒聊裡,Ali 才跟我說(內斂保守布農的她觀察了我許久),Manqoqo 家族裡有個私密的故事:不知多少年前,曾因一場瘟疫,Manqoqo 家族收留了來自平埔Kaxabu 的族人,兩方從此有了血緣關係。
我的母親來自埔里Kaxabu 族,從小,我就在濃濃的山林氛圍下長大。我外婆的長相,活生生就是從日人伊能嘉矩所拍的照片中走出來的南島人物。她捲髮,皮膚黝黑,喜戴金耳環,身材矮小但幹練有生氣。我自幼從神似魔法阿嬤的她那裡聽來了一堆村野神話,我們居住在環山的中海拔盆地,四邊皆是連綿中央山脈支稜,阿嬤說山裡有熊,熊是掌管森林的山神,風神有時化為豹,而有些樹木會自己走動,溪流易氾濫故族人仍普渡水神。儘管外婆一生主要操持台語,但當她去世時,我們調出來的戶口名簿,由外祖父母上溯的長輩們,名字下方都蓋了一個「熟」字。
後來我更認識了同住地利村的Lumav 牧師,他自稱祖先就是被布農人收養的Kaxabu 人。布農族詩人乜寇也認識Lumav,本來遍居於海岸與平原區的平埔族被認為與高山原住民族關係不深,但乜寇專文敘說了平埔與高山族人在古代有深刻地往來。
想來是上天讓我遇見Ali,這開啟了我的島嶼神話詩學,一個當代台灣人該如何溯源並肯認自己的島國神話?我便以一個十九世紀台灣中部山區村落為發想,上下求索。我開始遙想數百年前,Kaxabu 與布農密切往來的時期該是怎麼模樣。更甚,由數百年上溯數千年之際,當這座島嶼上的族群人們未如今日如此定型分布時(未有布農遑論Kaxabu),人類的生活狀態該是如何?我揣想著此島的人群分享著同樣神話傳說與生活方式,甚或洪荒之際,天地初始,眾神間的過活。
在人類古代,詩、思、神話合一是思維書寫的極致,印度《薄伽梵歌》、《羅摩衍那》,猶太《約伯記》,赫西爾德《工作與時日》等皆是人類書寫智慧的統合性代表。對於先蘇思想家,思與詩並沒有顯明的區分,「思想之詩」(poetry of thought)從古希臘開始便有著悠久的傳統,赫拉克利特尤是。作為詩人—思想家的原型,赫氏試著將言說迫向絕境(aporia),迫向語言邊緣的二律背反與不可確定,讓詩—思此雙面體的共生場域有至高的哲學與至高的詩歌運行其中。
我常懷想著詩—思想之人(penseurs poètes),此類特別的思維心靈在歐洲歷史上的首次湧現,語言逾越的塌裂處,思想的絕處及終點,詩—思想者在詩意與思意間實踐限界內外的跨越與探求。意即,哲學之先,「思」如何與「詩」為鄰?且神話如何轉譯為思?起源之前,思/詩/神話如何眾妙而同出?詩人,如何操作著凝神之思⋯⋯。我遐想著,回到思想與語言尚未區分的這種渾然一體的狀態。
一九三一年,時年二十五歲就讀東京大學二年級的鹿野忠雄來台登山七十天,他山行的範圍包含了今日丹大山、馬博拉斯山、馬利加南山、秀姑巒山壙埌的荒野(今南三段、馬博橫斷、南二段),因而寫下了大名鼎鼎的山岳著作。其中有個片段敘述,他同布農族獵人登頂中央山脈最高峰秀姑巒山時,遠望重疊的群山背後,金色燦然的太平洋也歷歷在目,那是東海岸。對一輩子從未離開過深山的布農族朋友,無論鹿野再怎麼解釋:
「Sikavaivi bunu.」(那是特別的天然積水)
「Madia danum.」(很多的水澤)
剽悍的布農人還是一臉未解,無法理解那銀色亂雲迆邐下,一大片藍色的東西是什麼。鹿野喜愛的布農朋友搖搖頭,高山族人不認識海。
而另一則小故事也讓我著迷。他們登山的途中,布農族人邊拿弓箭邊射獵藪
鳥,獵物中箭落地後,三名族人急忙趕上拿起鳥兒,「各拔掉一支羽毛,點火後分別放在自己的嘴邊吹出一口氣,舉行Sivinsaubu 儀式」,口中念念有詞,儀式是為了祈求能帶來獵捕到更多動物。
我曾拿著此文字片段詢問了幾位布農耆老。發現,竟沒有任何一位長輩能告訴我關於這樣祈求的細節,他們甚至沒有聽聞過這項狩獵儀式。短短九十年,我難以想像,這樣的捕獵祈求已在布農人之間永滅了。
兩個段落,完全顯示了百年前與今日宛如兩個異端遙遠永不相碰的星系之間口傳、記述、書寫、祭儀、世界觀等的塌陷並斷裂,絕處已是而無任何終點起點。
短短九十年,我們進入了嶄新全然不同的世界整體,我們已被框架限居在一個現代性的星球。我懷念著思想眾妙而同出一體渾然的狀態,那時候的人類沒摸過沒見識過「海」。
我遙想並深深懷念那樣的年歲。
這些年來,我總不滿足於一時興起的單一詩創作,而更是邁向更總體性之思寫。不滿足於一時乍現,一首一瞬間的思想,乃必須要躊躇塗改來來回回思索增補,最終以總體性定調而寫下。
這部詩組中的精神領域:山岳、森林、絕峰、狩獵、神話、基督宗教、現代性的失落,都是我這些年來來往往遭逢經歷的。詩集第一、二部分取材的多是南島各族共通的傳說神話;固然是因為神話之間的家族相似性。然而,我總是曲折塗寫,先發明了一些奇幻,才發現這些奇幻早已在口傳中形變許久,人的潛意識,有個集體的神話源頭。
我的祖父是祖籍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祖母是閩南人,我身上同時揉雜了平埔客閩及少數高山族的血統。實則,八成以上的台灣人本多是混血(唐山公、平埔媽結合的後代)。在城市裡求學就業,顯性,我們都是台灣人,但同時又擁有隱性的各樣認同(平埔閩客原民比例不一,詩中我用兩個空白□□指涉那不常說出口或漸被遺忘的自身)。整組詩篇中,第四部分的人物素描多出自我自幼以來身邊的親朋友人,我們多是由樸素村野到城裡去討生活的鄉下人,貧窮、骨力、台灣牛;我由隱性的混血認同一路上溯至千年之際的南島神話,一體兩面,即是顯性的若干台灣人之系譜沿革。當代台灣人真是無神話的民族?當我構思島嶼神話時,實不可能回到炎黃或中原的脈絡,那麼,由混血的自身一路上溯至南島洪荒(實際歷史中三、四萬年前最早的南島民族跨越冰河來到島嶼),便是當代集體台灣人所當肯認的詩/神話之開端,也即是我最初設定求索之源。
李維史陀曾說,人類學(anthropology)就是熵學(enthropology)(二字讀音一致)。熱力學第二定律,又稱熵增定律,第二定律認為熱量從熱轉冷是不可逆的,熵是測量其中不能做功的能量總數,在孤立系統中,能量消失不可逆,而熵總是增加的。若認為人類學就是熵學,則人類的存在就是代表著能量消逝混亂,熵數總是增加。那麼,神熵的年代,諸神消逝隱退,人世混亂,每況愈下,此世再無諸神容身之處。拔牙、文字、槍枝同出在I、III節,科學與現代性,神熵扭轉,對映曲筆之所在。除魅、現代性、上帝之死。我認為可悲的不僅是那神話的消逝,同樣亦哀憫著人類的景況。在神熵的年代,成為人未必能意識到其中的闕如。而在神熵的年代,若心靈盈滿神話,往往會成為現代社會的反芻殘渣,或不合時宜的一無是處,神熵之世,人殤/傷之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