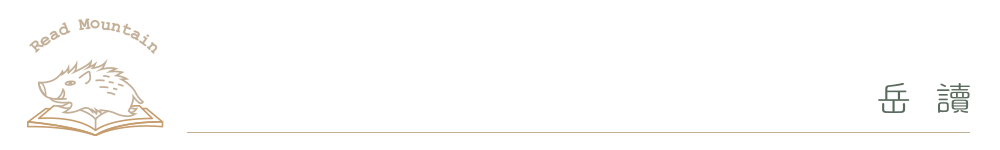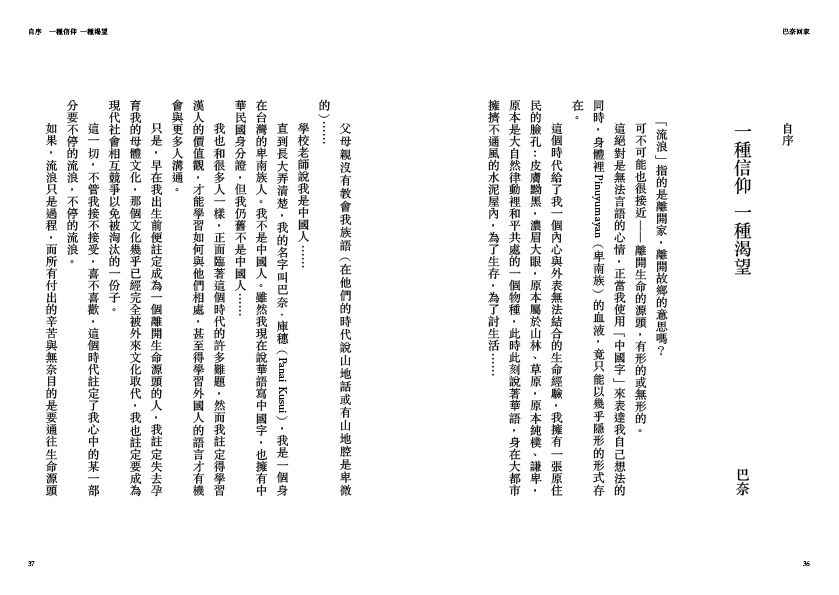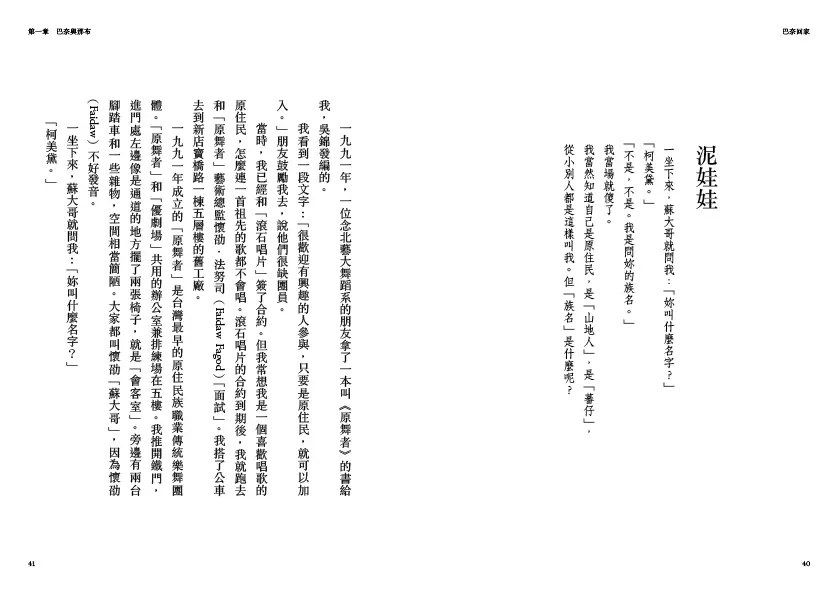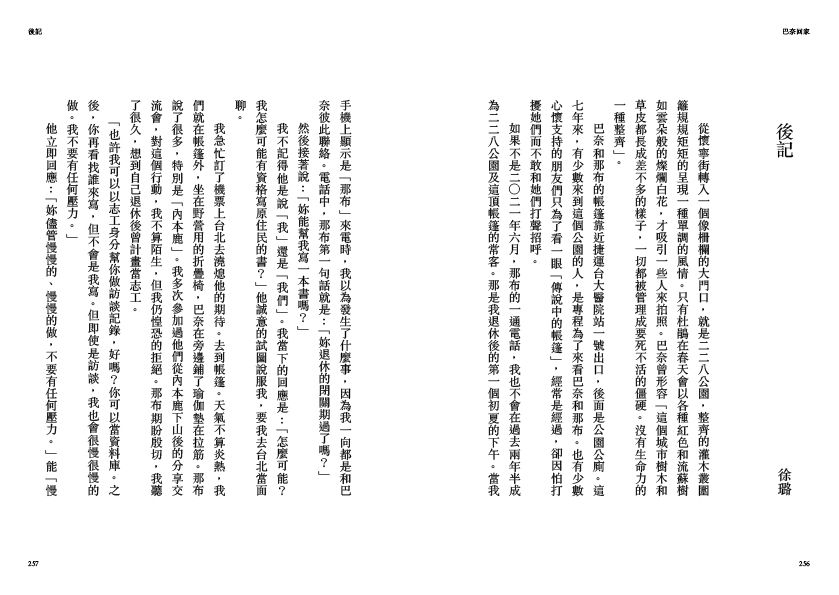商品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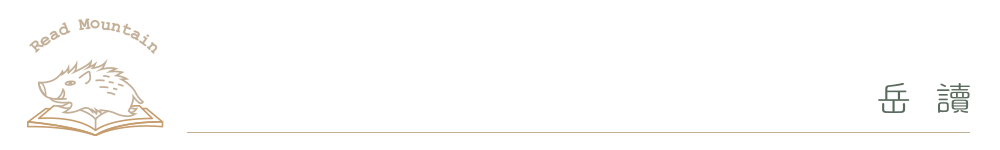

讓人熱血沸騰的書!
這是巴奈的生命故事
也是許多原住民族生活和歷史的縮影
希望這本書可以讓我們的聲音,
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
在回家的路途上,接續往前走,
為了文化的傳承,為了族群的尊嚴。
「妳叫什麼名字?」
柯美黛。
「不是,不是,我是問妳的族名?」
我從小知道自己是原住民,但「族名」是什麼?
以〈流浪記〉聞名歌壇的巴奈,從自我認同的迷惘裡走上族群命運的反思與奮起。為了原住民族的「尊嚴」、為了「轉型正義」、為了要求政府「完整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二○一七年起,巴奈與那布走上凱道,經過警方多次驅離,最後轉進二二八公園的角落,抗爭運動逐漸從焦點轉向邊陲。
她和那布在帳篷裡歷經四季寒暑,甚至曾經「睡在沒有屋頂的地方」,他們堅持了七年、超過二千六百個日子。
很多人問:「你們還在?」
是的,依然在。
漫長歷史上,原住民族從原來的聚落被強制遷徙,「被迫」放棄名字、語言、祖先的承繼,在從屬於他者的生活方式裡,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歷史記憶、傳統和山林文化……抗爭七年間彷彿過去處境重演,他們的身影在不斷地驅趕中遠離大眾的視野,但這次,已經踏上「回家」的腳步將不會停。
這本書首度寫出巴奈的成長故事,更寫出原住民族群被迫離開家園、失去土地的歷史。這是一本讓人熱血沸騰的書,也是原住民族生命和歷史的縮影。
專文推薦
李雪莉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
洪廣冀 台灣大學地理資源環境學系副教授
馬世芳 作家、廣播人
熱血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ABAO阿爆 排灣族創作歌手
安溥 歌手
李屏瑤 作家
林懷民 雲門舞集創辦人
阿女烏 作家
苗博雅 臺北市議員
張培仁 中子創新/街聲創辦人
詹順貴 環境律師
楊雅喆 導演
蔣勳 作家
各界感動推薦
《巴奈回家》意義深遠。巴奈強調的「傳統領域」喚醒我對原住民文化的尊重。
「傳統領域」的核心價值,是不是回到人類敬重天地的初衷?
節氣秩序、生態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
一起讀《巴奈回家》一起隨巴奈親近土地、海洋,親近樹木與岩石,親近風、雨、花朵與陽光。──蔣勳(作家)
聽巴奈那些深深穿透你的歌,聽她訴說半生的流離、失根的傷痛,我才意識到這片土地上持續不斷的掠奪與侵害,遠遠還沒有結束。她為傳統領域劃設爭議持續靜坐抗爭兩千多天,老實說,我也有過不解:總該有更能體現「效率」與「效果」、更能遂行「整合」與「溝通」的「運動策略」吧,非得如此自苦嗎?
讀完這本書,我想我懂了:這不是所謂「運動」的「成功」或是「失敗」的問題,而是攸關「尊嚴」──那是凜然不容侵犯,不能讓步的底線。──馬世芳(作家,廣播人)
二六四四天是抵抗與救贖同步在進行。抵抗時不免受傷,但那之後所獲得的自知、勇氣、救贖,會豐富自己並感染他人。《巴奈回家》很珍貴地成為原住民族回家之路的火種。
希望這個運動所召喚過的人們,以及有機會閱讀此書的朋友,除了感知原民朋友的受苦經歷外,還能為族群主流化的平等理想一起努力。──李雪莉(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
我認為《巴奈回家》也是一部關於survivance(「在困境中的」生存)的作品。跟著巴奈的敘事,你從台南至台東,從台北至紐約,再落腳在凱道與二二八公園。除了內本鹿的山,你也拜訪了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地下音樂界,乃至於Covid-19肆虐下的二二八公園。你體會到,就巴奈與那布而言,回家是為了生活,生活是一系列的抵抗,抵抗同時也是生活。──洪廣冀(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作者簡介|
巴奈 Panai Kusui
歌手、詞/曲創作者、原住民族權利倡議者等多重身分。年輕時流浪在城市之間,獨自面對恐懼、焦慮,與來自原住民族血脈的身分。作品色調濃重沉鬱、簡單坦率如利刃,直指寂寞與對自我的反覆質疑。在台灣多項人權、環境運動上,她都選擇挺身而出,以音樂做出宣告與反抗。2017年起為《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土地問題,於凱道、二二八紀念公園紮營抗議超過2600天。
個人全創作音樂專輯有《泥娃娃》(2000),2020年發行的《愛,不到》於次年獲得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2020年度十大專輯、入圍第32屆金曲獎華語女歌手獎並獲得第12屆金音創作獎評審團獎殊榮。
2017、2018年在抗議期間於街頭深夜錄音完成EP《凱道上的稻穗》、《凱道巴奈流浪記》。2021 年新冠疫情期間,巴奈在社群發起「寫一首新歌直播計劃」,而後與好友組成「青山在co.」樂團,獨立發行專輯《沒有依靠的人》。2023年有感於原住民國中生自殺事件,發表單曲〈你說你又沒有推他〉(feat. 巴大雄)。其它音樂作品與音樂製作還有《停在那片藍》(2008)、《Message》樂團同名專輯(2008)、《Niyaro nu wawa》小孩子的部落/都蘭阿美族語童謠專輯(2014)。2024年與金曲製作人柯智豪合作推出首張台語專輯《夜婆》。
徐璐
基隆出生長大,高中畢業後離家去念淡江大學英文系,當時是淡江文理學院。受到導師王津平、李元貞等人的影響,開始關心社會議題,拿起相機走訪鄉鎮。
擔任過《八十年代》主編、《自立晚報》記者、台北之音台長、華視副總及總經理。在報社時期曾經受邀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
40歲後,每年都會存錢用來實現自己一個人漫遊歐洲旅行的夢想。
48歲時,大學時代累積的能量化成召喚,開始投入與文化、鄉鎮有關的「中華電信基金會」,及「台灣好文化基金會」。
出版過:《歷史性、大陸行》、《北京最後採訪》、《暗夜倖存者》、《我的台東夢》。
56歲時移居台東。62歲時決定退休。現仍定居台東。
|目錄|
推薦文 為族群主流化的平等理想一起努力/李雪莉
推薦文 跟著巴奈回家/洪廣冀
推薦文 往前走,別回頭/馬世芳
自 序 一種信仰 一種渴望/巴奈
第一章 巴奈與那布
泥娃娃
流浪記
那布/說故事的人
第二章 重返內本鹿
Na Kulumah我們要回家了
蓋自己的家屋
附錄:被消失的內本鹿
第三章 總統的承諾
蔡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
走上凱道
第四章 我們不是來鬧的
凱道一百天
在二二八公園流浪
在帳篷的廟宇裡
後記/徐璐
訪談紀錄
感謝的話/徐璐
巴奈與那布感謝名單
|序|
序
一種信仰 一種渴望
「流浪」指的是離開家,離開故鄉的意思嗎?
可不可能也很接近——離開生命的源頭,有形的或無形的。
這絕對是無法言語的心情,正當我使用「中國字」來表達我自己想法的同時,身體裡Pinuyumayan(卑南族)的血液,竟只能以幾乎隱形的形式存在。
這個時代給了我一個內心與外表無法結合的生命經驗,我擁有一張原住民的臉孔:皮膚黝黑,濃眉大眼,原本屬於山林、草原,原本純樸、謙卑,原本是大自然律動裡和平共處的一個物種,此時此刻說著華語,身在大都市擁擠不通風的水泥屋內,為了生存,為了討生活……
父母親沒有教會我族語(在他們的時代說山地話或有山地腔是卑微的)……
學校老師說我是中國人……
直到長大弄清楚,我的名字叫巴奈.庫穗(Panai Kusui),我是一個身在台灣的卑南族人。我不是中國人。雖然我現在說華語寫中國字,也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但我仍舊不是中國人……
我也和很多人一樣,正面臨著這個時代的許多難題,然而我註定得學習漢人的價值觀,才能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甚至得學習外國人的語言才有機會與更多人溝通。
只是,早在我出生前便註定成為一個離開生命源頭的人,我註定失去孕育我的母體文化,那個文化幾乎已經完全被外來文化取代,我也註定要成為現代社會相互競爭以免被淘汰的一份子。
這一切,不管我接不接受,喜不喜歡,這個時代註定了我心中的某一部分要不停的流浪,不停的流浪。
如果,流浪只是過程,而所有付出的辛苦與無奈目的是要通往生命源頭的路,我會乞求總有一天,能有這樣一天。
在凱道和二二八公園七年。七年大概是我十分之一的人生──用來跟這個社會溝通,讓人們有機會了解這個國家對原住民族權益的漠視。你可能不同意,無法理解,我們生來就被時代奪去的文化,對我而言是多麼珍貴。
我想,感受過失去,感受過無法回復的人應該就會明白,覺得美好將要消失的一種急切、無助與不捨。
我渴望與母體文化相融的機會。在母體文化裡生活,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渴望。
|詳細資料|
ISBN:9786263961555
叢書系列:新人間
規格:平裝 / 288頁 / 14.8 x 21 x 1.83 cm / 普通級 / 全彩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第一章 巴奈與那布
泥娃娃
一九九一年,一位念北藝大舞蹈系的朋友拿了一本叫《原舞者》的書給我,吳錦發編的。
我看到一段文字:「很歡迎有興趣的人參與,只要是原住民,就可以加入。」朋友鼓勵我去,說他們很缺團員。
當時,我已經和「滾石唱片」簽了合約。但我常想我是一個喜歡唱歌的原住民,怎麼連一首祖先的歌都不會唱。滾石唱片的合約到期後,我就跑去和「原舞者」藝術總監懷邵・法努司(Faidaw Fagod)「面試」。我搭了公車去到新店寶橋路一棟五層樓的舊工廠。
一九九一年成立的「原舞者」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職業傳統樂舞團體。「原舞者」和「優劇場」共用的辦公室兼排練場在五樓。我推開鐵門,進門處左邊像是通道的地方擺了兩張椅子,就是「會客室」。旁邊有兩台腳踏車和一些雜物,空間相當簡陋。大家都叫懷紹「蘇大哥」,因為懷紹(Faidaw)不好發音。
一坐下來,蘇大哥就問我:「妳叫什麼名字?」
「柯美黛。」
「不是,不是。我是問妳的族名。」
我當場就傻了。
我當然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是「山地人」,是「蕃仔」,從小別人都是這樣叫我。但「族名」是什呢?我有好多問號。
「原來我沒有名字!」
「怎麼會有人沒有名字?」
「現在,還有多少人沒有名字?」
我回去問了阿美族的母親,她才臨時幫我取了「巴奈」。巴奈是稻穗的意思,原住民的菜市仔名。
我進了原舞者,全職,月薪一萬五千元。那年我二十六歲。
我的父親是卑南族,但我在台南出生。小時候,台語是我的母語。六歲時,我自己回到台東縣初鹿部落的家。
那是個小村落,台九線經過,也有初鹿火車站,街上有幾家公路餐廳和雜貨店。
從我家出去,不到三分鐘,就是大馬路。路旁都是麵店、自助餐店、檳榔攤、快炒店,現在那裡也開了三家超商。
初鹿國小唸到三年級,望女成鳳的媽媽把我轉到馬蘭國小,台東市的明星小學。
父親常請朋友來家裡吃飯。吃完飯,父親會叫我在桌旁唱歌給大家聽,我就唱〈泥娃娃〉。唱完,父親會給我五塊錢,我和同學可以買好多零食。所以即使沒有客人,我也會跑去跟他說:「我還要唱〈泥娃娃〉。」
轉校沒多久,父親改當大卡車老闆,公司有四輛大卡車,那是家裡比較不窮的日子。父親僱了好幾位司機和助手,油錢之外,卡車常常需要修理,父母親一直在周轉錢。但家裡有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我每天都偷偷自彈自唱。
有客人來吃飯的狀況維持不到三年。父親的車行倒閉,負責開支票的媽媽因《票據法》坐牢半年。小學六年級時,父親帶我和哥哥離開台東,搬到玉里。
我記憶裡最常停留的畫面是剛到玉里時,父親租來的那間鐵皮屋。破舊、窄小,我們三個人擠在一起,又熱又濕。後來,在學校讀到「家徒四壁」這四個字,我立刻想起我自己的家,什麼都沒有,有時還需要向鄰居借電。沒借到電時,我們只好點蠟燭,那種颱風來時常用的紅色蠟燭,為了怕油滴到地上,我讓它站在鱷魚蚊香的鋁罐裡。
洗澡要用熱水,用一個鍋子放在瓦斯上燒。有一次,我沒拿好鍋子,滾燙的熱水倒到我腳踝。我不知是從哪裡聽過的,就拿醬油去淋。家裡都沒人,沒有看醫生,我到現在還有一大塊褐色的疤痕。
小小年紀的我知道哭沒有用。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
窮到什麼都沒有,是我的童年。小學六年級快結束時,父親要我拿兩千元到初鹿,給隔壁的大伯母拜拜。我看見家裡大門被貼上黃色的封條。沒有大人提過這件事,我也裝作不知道。
父親成為被僱用的大卡車司機,工作的地點有時在石礦區,也做過北迴鐵路,南迴鐵路。哥哥國中畢業後,也跟著父親當助手。從初鹿到玉里,我換了四所小學。父親和哥哥早出晚歸,在家的時間不多,回家都已筋疲力竭。我必須負責買菜,料理晚餐。
沒人可以說話,也沒人聽我說話,我自顧自的彈著吉他唱歌,想像自己抱著一個洋娃娃。父親在週末或連假時,會載我一起去山上的工地。卡車很破舊,連我腳踩的地方都有一個破洞,車子跑起來的時候,看得到疾速退後的馬路。
為了不想讓「窮」這個事情被人家看見,我會故意對周遭的事物顯出一種冷淡。同學在我旁邊吃冰棒,我就露出一種不屑的表情。其實,那是故意「跩」出來給別人看的。
在玉里讀完國中後,我回到台東初鹿部落的家。媽媽出獄後有十多年沒回到我們的身邊。唸台東女中的我有時住宿,有時通車。若回初鹿的家,晚餐就在隔壁大伯家和他們一起吃。
我高一時,哥哥在石礦區的產業道路上發生意外,走了。我感覺自己沉入大海,我沒有慌亂,只覺得自己進入一個很緩慢的世界,我的身體和呼吸都慢慢凝結,一切被凍成大冰塊,靜止不動。我動彈不得。
我一直不敢問,成長的過程也不敢去想,或去談這件事。長大以後,我才讓回憶慢慢在潰堤的淚水中浮上來。
發生事情後,大人什麼都沒說。我到現在仍無法理解,為什麼大人沒有好好照顧小孩?為什麼沒有讓哥哥好好的長大,就讓十九歲的他去做這麼危險的工作,獨自開著十六噸的卡車,載著二十五噸的大理石,死在懸崖邊上。
我知道哥哥這麼拚命是為了賺錢。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窮?這是命運嗎?
我記得哥哥的遺體被清理過,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內都是土。我可以想像他在翻車的那一瞬間,應該很痛苦的抓著地上的土,掙扎著要活下去。
他出事後,我每年都會去放置他骨灰罈的廟裡,持續了十幾年。有一天,我夢見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醒來後,我告訴自己他應該已經過得很好,應該不要再對他有這麼多不捨了。最後一次去靈骨塔,我就對他說:「哥,我以後不會來了。你的事,我要放手了。」
哥哥過世那段時間,我特別想媽媽。我開始一個人在週末或連假坐國光號走南迴去高雄找她。國光號在屏東楓港會停十五分鐘,我就下車買烤小鳥和茶葉蛋。
有一次,黃昏時刻,我在楓港的海邊看見太陽落下的景色,大吃一驚。在東部,太陽一向是升起來的,我從沒看過太陽落下去。我從沒想過,原來山的那一邊是另外一個世界。原來真正的世界不是我原來所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