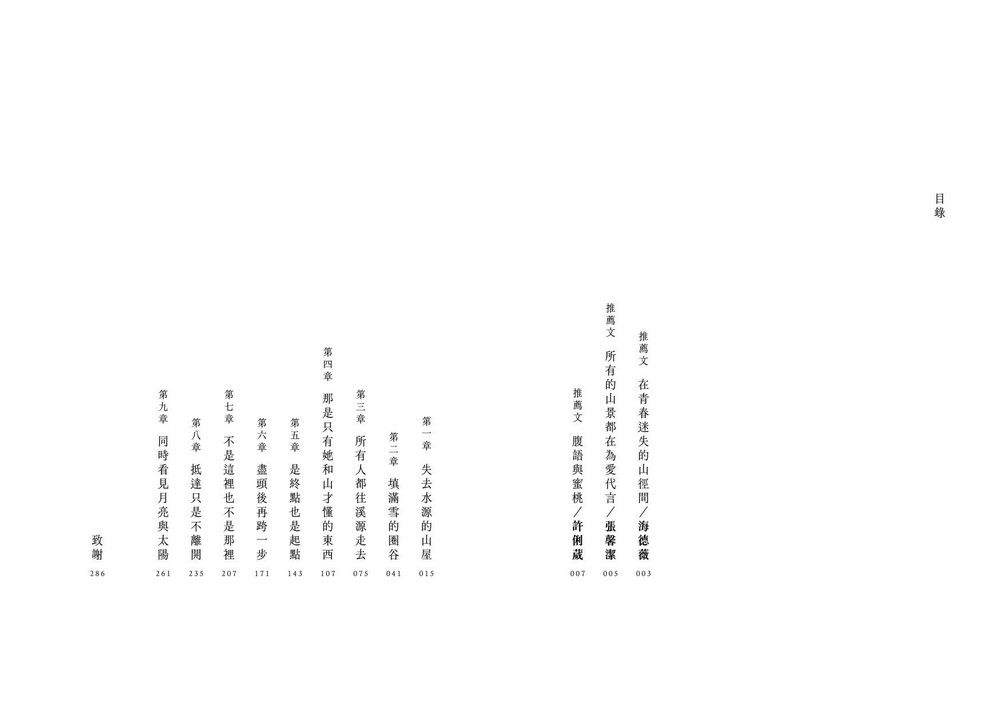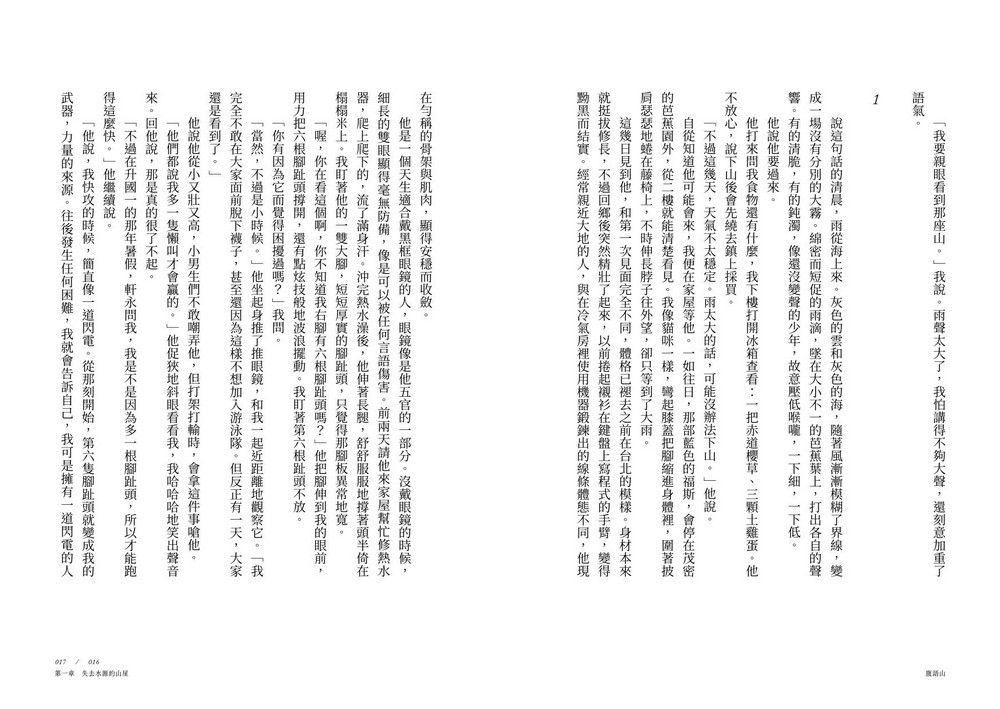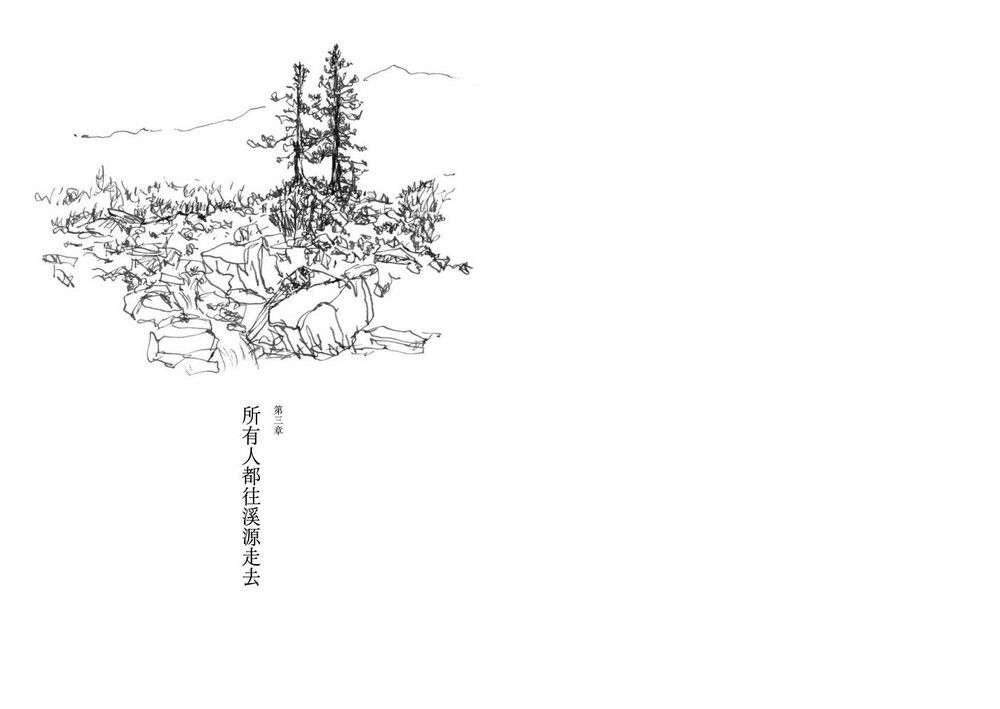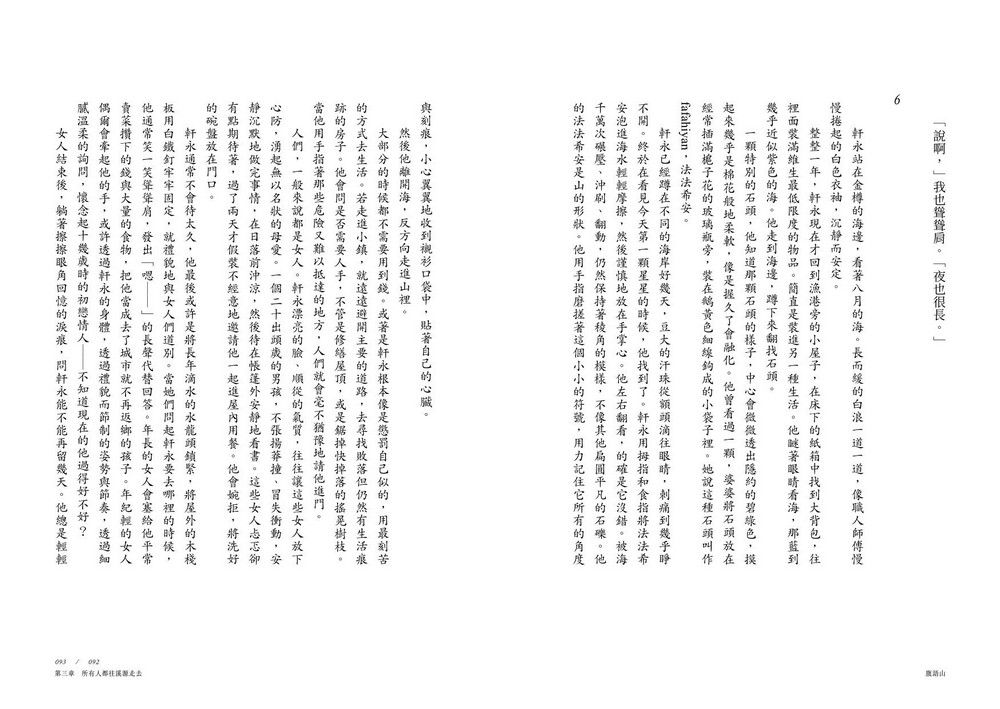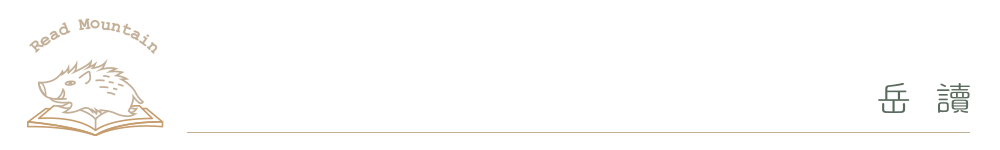

海儘管遼闊,山儘管深遠,星空儘管神祕
但愛是比它們更大的東西
山女孩Kit首部小說創作
在山之間,寫下關於愛的魔幻體驗
「我要怎麼讓你明白,你與他從來就不是先來後到的問題。」
如果不是十五歲的那件事,
他們三個人,不,是我們六個人,
應該還是能維持表面的和平,
一直那樣生活下去吧。
.一部把「愛」具象化的成長小說
青春時期對於愛,是大膽、美麗、義無反顧的經驗與想像;長大後或許不敢那樣子叛逆地談愛,但不代表沒有探索的欲望。當愛變成扭曲隱晦的情感、某種影響人生選擇的羈絆,甚或忍讓求全的腹語,小說想探問:我們能不能理解各種不同形式的愛?我們能不能直視,愛有時候就是那樣難以言喻的混亂?
.透過山徑,走進心裡最幽微的角落
走進書中的山,是疫情期間引發島內登山風潮的郊山縱走,是台灣熱門的百岳路線嘉明湖,是前往尼泊爾凝望神山群峰。海拔一千、三千到六千,不同的高度、景象與心境,從生活啟程到生死探問,每一趟山行,我們都將遇見層層豁然的自己。
.不要阻止,這是屬於我們的追尋
在青春迷失的山徑裡,我們將如何展開自身的追尋?往前的人、等待的人,與不知道要追求什麼的人,真的有好壞對錯嗎?隨著年齡的變化、情節的展開,我們將看見書裡每個人生命底層的祕密。那或許衝撞激情,或許保守壓抑,但此般不理智與執著的點燃,其來有自,不要放下,就去找答案。
∴
青春時期,我以為父母沒發現我們這樣偷偷地愛著,
長大之後,才明白他們也是那樣隱密而無聲地愛著。
「你什麼時候發現我知道的?」
「為什麼你要讓我覺得,愛是一件不對的事情呢?」
這是傅宇珊二十九歲前的故事。她與住在台東的林軒永從小就認識,見面時總是從山裡玩到田裡,從溪邊離開再去海邊。他們的媽媽也情同姐妹,一起從最頂尖的高中淪落到不怎樣的大學。直到發生了那件事,兩個人的影子,都分別與另一個人重疊……
三個點,可以組成一座山的形狀。三個人,會如何在這座山中聚首、來去?小說巧妙利用「三」作為引線,寫下三人之間的羈絆、三種高度的追尋,甚至回溯主角所在的當下、上一代,以及上一世。我們或許還不明白,此刻對彼此的感覺是否都叫作「愛」,但有時候,流傳下來的言語、留在大自然中的記號,既是指引,也是生命要你體驗的答案。
展望推薦
王浩一|作家
宇文正|作家、聯合副刊主任
林婉瑜|詩人
徐珮芬|詩人
栗光|作家、聯合報繽紛版主編
海德薇|編劇作家
郝譽翔|作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高耀威|「書粥」老闆
張馨潔|作家
許俐葳|小說家、《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
陳栢青|作家
雪羊|山岳作家
劉克襄|作家
劉崇鳳|作家
TaiTai LIVE WILD 楊世泰&戴翊庭|《山知道》作者
【她們讀《腹語山》】
★在抵達與停留之間,我們可以找到許多關於美的細節,神祕並且細膩。──徐珮芬/詩人
★十五歲的愛與欲望,二十歲的追尋和迷茫,讓讀者彷彿在迷霧中好奇穿梭……在呢喃絮語中展開,擁抱野心十足的浩瀚題目。──海德薇/編劇作家
★小說深刻地探尋愛情之中的三角關係……沉默的山蘊藏的細密訊息,正如關係的迷藏裡,說不出來的話才是最真實的心聲。──張馨潔/作家
★誰不是倚靠著什麼在活著?腹語和蜜桃,苦與甜,同時在這本小說裡展現各自的面貌,但都是人生的模樣。──許俐葳/小說家、《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
★讀《腹語山》到後來,山的氣味遠去,我被作品濃烈的羈絆與執著緊緊牽制……很久沒這樣投入於小說了。──劉崇鳳/作家
|作者簡介|
山女孩Kit(方妙)
台北人,生於清明穀雨之間,卻不喜歡雨。學不會星盤,選擇山與薯條。喜歡庸俗的字,比如永遠,比如愛。
著有《山之間》、《沒有名字的那座山》兩書。作品已有韓文譯本。近年獲國藝會文學補助,試著以寫字為生。
Instagram|kit_fang
Facebook|山女孩
|目錄|
第一章 失去水源的山屋
第二章 填滿雪的圈谷
第三章 所有人都往溪源走去
第四章 那是只有她和山才懂的東西
第五章 是終點也是起點
第六章 盡頭後再跨一步
第七章 不是這裡也不是那裡
第八章 抵達只是不離開
第九章 同時看見月亮與太陽
|序|
推薦文
在青春迷失的山徑間
海德薇/編劇作家
山,容易讓人擺脫偽裝,山裡發生的事最能夠反映真我。這一次,山女孩Kit跨足小說,預備征服另一座文學山頭。以揭露本色的名字發表,令人驚喜不已,相信讀者朋友也十分期待。
有幸先睹為快,故事中時序跳躍,現在和過去交織錯落,營造出一種魔幻色彩。我喜歡故事中文字的躍動感,順暢地銜接了不同場域和時間跨度,都市和森林,海到山,態度自由,一如角色們的不羈。
翻開書頁,開章以為講的是年少懵懂的愛情,由一個揪心的事件展開,但,隨著訊息量的拿捏釋出,漸漸發現沒那麼簡單。作者想談的不只是愛情,似乎更接近純粹的愛的探尋。
宇珊、軒永和阿樹,多年後試圖撿回遺落的青春,可是三個人的愛怎麼成行呢?愛有多大?跟山一樣大嗎?愛是什麼?可以被度量、比較,被切割、分享嗎?
《腹語山》透過三位主角、三個世代的關係和故事來呈現愛。其中,少年的浪漫情懷寫得很好,帶有清新詩意,其筆下刻畫十五歲的愛與欲望,二十歲的追尋和迷茫,讓讀者彷彿在迷霧中好奇穿梭,試圖探索出一條路來。這種尋路的過程,也好似在山中探勘路徑。
書中「愛,但是不喜歡」,以及「痛是愛的變形,痛也是不愛的變形,這世界不存在不會痛的追尋」的概念,非常真實且真誠。山有靈,能映照內心,我們只能聆聽靈魂深處的聲音。人在山中,無處可逃,主角們自然也得直視內在不忍揭開的脆弱面,諸多描繪必然能引起愛山之人的共鳴。
闔上書頁,餘韻蕩漾,特別難忘嘉明湖畔的場景,是最原始純淨的自然洗滌。不禁想起布農族征伐太陽的傳說──被射中右眼的太陽變成月亮,每晚都會回來嘉明湖看看自己被射的箭傷。嘉明湖被布農族人稱作「月亮的鏡子」(Cidanuman Buan),我想,我們無法對嘉明湖說謊,書中人物也不能。
讀畢會發現,作者在書中探討了愛的本質,留給讀者無限省思。《腹語山》是女主角傅宇珊青春成長,既關於山,也關於腹語,腹語暗喻那些說不出口的情感。這是一個深刻、動人的故事,在呢喃絮語中展開,擁抱野心十足的浩瀚題目,推薦給各位讀者細細品味。
推薦文
所有的山景都在為愛代言
張馨潔/作家
我想像過無數個在山上紮營的夜晚,當風聲也寧靜的時候,各樣待解的人生謎題塗銷掉山林的聲音,天幕上毛孔般密集的星辰好像一舒一收的在呼吸。那一刻,是否正是命運的後台管理系統,運作校正的時刻呢?
那些勘不破的人際隱微繫結,在某些神秘時刻裡擾動著。小說中主角傅宇珊在夏威夷旅遊,遇見了青年查斯。一個夜晚,月光如同浪花打入房間,查斯在熟睡中與她相擁。這副陌生軀體,在一瞬間使她感知,這是來自另一位所愛之人的擁抱。
另一個時刻,已故的西藏少女木柰與男主角軒永在同一個空間,影像重疊、彼此凝視,他們都明白對方不是幽靈,而是另一個不同時空中的房間住客。身體只是靈魂的載體,前者會腐朽,而後者累世歷劫。偶有那樣的感應時刻,無法說清又讓人深信不疑。
站在山之前猶如站在情感之前,文中所有的景色與未知,都是在為愛代言。小說深刻地探尋愛情之中的三角關係,將現世不可解的糾葛,綿亙至世代,直至前世,為有限的今生爭取更寬闊的解讀。大音希聲,沉默的山蘊藏的細密訊息,正如關係的迷藏裡,說不出來的話才是最真實的心聲,彷彿腹語,藏於表象之下。
作者慧黠的文筆中,山脈有著各式的植被與景貌,隨著山勢與氣候的交集,衍生出各樣的行途經驗。即便知道走向山意味著走向危險,但主角們逐漸接受,走向山找尋答案是必經的歷程。而即便懷著再虔敬的心,面對屬於自然的不可測,終究有人迷失在山裡。
作者將小說寫入山林,帶著我們走入山裡,走進自然裡,展示了自然的瑰麗與神異。自然如此凶險,愛的流動也是自然,但愛讓人掙扎,又讓人渴望追尋,如同山林的召喚。
推薦文
腹語與蜜桃
許俐葳/小說家、《聯合文學》雜誌副總編輯
這是一本有著兩種聲音的小說,所有人說出來的話語都有著雙重意思。一開始,我們不知道說話的人是什麼身分,不知道抵達家屋的人和林軒永是什麼關係,隨著情節推進,才發現裡頭有些情緒和反應不太對勁,人與人的關係是那麼甜美,但又如此撲朔迷離。
這自然是作者的精心設計,我們跟著少女傅宇珊去探索、去追問,然後等待和命運之人的再次相遇。小說有著剛剛好的懸念,這些懸念多是關於人的,或者說,是關於愛的。當他們試著去愛誰,去理解誰,有些懸置的祕密,會以意外的方式展開,愛原本就是一種推理的過程。
然而,愛的真相不一定盡如人意。有些情緒是隱性的,是長年藏在祕密底下的影子,是痛苦的腹語,「我就這樣活著,不發一語地活著,把自己沉在水最深的地方,於是所有的聲音聽起來都如同腹語。」
腹語乍看是一種隱而不宣的壓抑,但其實也是另一種訴說的途徑,在混亂中,逐漸將自己一層層褪下,重新長出力氣,也才有前進的可能。試著為所愛之人煮一碗麵,在深山裡遞上一杯熱奶茶。《腹語山》有許多關於山的深刻描寫,讀這本小說的過程也像登山,必須要花費力氣,兜兜轉轉才能抵達心的深處。有些人,在山上才會說出真心話;而有些關係,要下了山才見分明。
我非常喜歡小說裡頭,傅宇珊的同事向她描述幸福的片刻,一個讓自己撐下去的理由:「你要從內心深處去挖出曾經發生過的場景,然後用雙手牢牢握著。像我呢,就是握著一顆水蜜桃。」簡直不能更可愛,又極其精準地寫出了人生的現實——誰不是倚靠著什麼在活著?
腹語和蜜桃,苦與甜,同時在這本小說裡展現各自的面貌,但都是人生的模樣。祝福以新名字出發的方妙與她的寫作。或許文學與山,都是她的那一顆水蜜桃。
|詳細資料|
ISBN:9786263617506
叢書系列:綠蠹魚
規格:平裝 / 288頁 / 14.8 x 21 x 1.5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我仔細回想起來,的確就在小學畢業升國中那個暑假,軒永變了。像是掩飾不穩定的變聲期,準備脫離一切舊殼去迎接所有嶄新的彆扭少年。後來即便我回去台東,他也鎮日泡在新認識的同學家。
就在那個夏天,我第一次留長了頭髮。穿上私校的百褶裙和黑皮鞋,除了鋼琴課,放學也跟著同學去老師家裡補英文和數學,回到家還要準備各科小考。終於配了眼鏡,金框,細邊,沒有任何特色,像媽媽以前一樣。
從此以後在台東,我們看到對方就沉默,像兩只在海底深處的大蛤,見到面只是一聲簡短的嗨,一開一闔間冒出微弱的氣泡,從海底無力地飄向天空。甚至到後來,他連點點頭示意都沒有,只是遠遠凝視,當我回看時就別過眼,試著漠視我,或表現得毫不在意。我也只能裝作毫不在意。沒關係的,我對自己說。我從不知道為什麼,但那時候我只能讓他那樣做。
即便如此,我還是可以感覺到他。他一聲咳嗽或一個轉頭,一本隨手擱在二樓長廊的書,或一處被他溫熱的角落,這樣就夠了。我永遠能從空氣裡的撲滿,捕捉他存下的話語。那是什麼東西,我很難用言語去說明。那些訊息存於過去與未來,流動與靜止之間,在非常微妙的間隙,我知道只有我可以去提取。
這樣的狀況持續兩年,直到國三那年寒假。按照慣例,小年夜我家和庭庭阿姨一起先回台東。晚餐過後,家屋裡塞滿了大人,他們帶著食物來向高婆婆拜年,但其實是想要有個地方徹夜喝酒。一樓鬧哄哄的,屋子裡到處都是酒杯和空酒瓶,簡直像夏天的豐年祭。家屋沒有電視,葵早早去了鄰居家,準備看整夜日本台的紅白重播,我在房間找到庭庭阿姨的舊MP3,戴著耳機坐在二樓,在長廊黃黃暗暗的燈光下看書。
那一晚的所有細節,我從沒有忘記過,只要閉上眼睛,場景就能瞬間切換。
夜裡,墨色的海浪打上沙灘,空氣中夾雜著燃燒的龍眼木與泥土的氣味,芭蕉園裡葉片斷裂落地,山羌的鳴叫短促如狗。我甚至完全記得坐在外廊時,耳機響起鐵與酒樂團的《Naked As We Came》,前奏綿密的吉他聲。
高婆婆帶著一樓的歡愉,臉頰紅紅地爬上二樓,喚著關在房裡的軒永,帶看起來無聊的我去海邊放鞭炮。她似乎還把十五歲的我們當做小朋友。「去玩啊,你也不要大過年的還在讀書,多掃興!」高婆婆硬把我們推下樓,我連外套都還來不及拿。
我戴著耳機,縮著脖子,雙臂緊緊抱在胸前,走在軒永身後。一向惱人的東北季風停了,剩下乾乾的冷。山裡沒有燈,從山上一路走到台十一線的小馬橋至少要半小時,橫跨了小馬橋才會抵達海邊。
這一條曾被颱風沖刷、各種小貨卡疾駛的泥土路,一直都不好走。下過雨後,車子開不上來,大人都會笑這條路殘廢了。在沒有路燈的黑夜中,我低著頭走在殘廢路上,踉蹌了好幾次。小路兩旁長著高過人的扶桑花叢、結著碩大果實的波蘿蜜樹,沒有風的冬夜,各種氣味黏膩逼人。一直像緊閉大蛤沉默著的軒永,突然停下來,我也跟著停了下來。
十五歲的他,耳朵豎在清瘦臉頰的兩側,下巴的線條變得剛毅而深刻。他穿著一件長至膝蓋的黑色風衣,帽兜套在頭上,雖然沒有比我高多少,不知怎麼的,身影看起來已經像個大人。
但那時候,我們就只是兩個彆扭的青少年而已。他在黑夜中轉身往我走來,在離我半步的距離脫下外套,遞給我。我摘下耳機,慢吞吞地把雙手套進還留有體溫的黑色風衣。他把手插進褲子鬆垮的口袋,等我穿好後,靜靜地對我伸出左手。我凝視著他,這次他沒有躲開。只剩下一件單薄長袖的他,手心卻溼溼熱熱,像一條夏日午後被陽光晒溫的小溪,我的手泡在溪裡,也暖暖軟軟的。
他牽著我,安靜地越過小馬橋,往海邊走去。錯落在田中的農舍,這時都亮著溫暖的燈光,飄來食物的甜香。
沒有風的夜裡,天空有逗留不去的微小雲塊,我們並肩走在一起,我偶爾抬頭看看他,他睫毛低低地回望我。我不明白為什麼,但我會全部接受。
退潮後的沙灘,被銀白色的月光晒成一面黑色的鏡子,浪緩緩爬上岸,像是慢動作一樣地捲起沙子,發出刷──刷──的聲音。月亮太亮,幾乎看不到星星,深色的雲層壓在遠遠的海際線上,月色把墨水般的太平洋染上一層金屬般的質地,反射出一道海上的銀河。所有的物質在夜裡看起來更沉靜,粼粼的浪邊緣鑲嵌著溫潤的光澤,像是濃厚柔美的乳脂。軒永幾乎是貼著我的手臂,緊捱著坐下,沒有風吹亂他額前軟軟的長髮,他精緻的側面像女孩。
「抱歉。」這是他開口的第一句話,並看了一眼空空的雙手。
「沒關係,」我說:「又不是小孩子,我也不特別愛鞭炮。」
「我不是為鞭炮道歉。」他低低地說。
我望進他的眼睛,他把話語吹向我。我們交換彼此的風,填滿了過去的空白。
「好長的一段時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他沉默了好一陣子。
「直到有人告訴我,海灘上每一顆石頭都長得不一樣,但都有一顆最特別的石頭。在遠遠的大海裡游泳時,要認得那顆特別的石頭。大浪打來的時候,一定要先睜開眼睛才能呼吸,然後眼睛絕不可以離開那顆石頭。
「我想了很久,我猜,你就是海灘上那顆特別的石頭。因為大浪打來的時候,我的眼睛只看得見你。」
軒永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的心臟發出了像非洲遷徙般,數萬頭獸一起奔向水源,轟隆轟隆的聲音。
我很害怕他會聽見,憋著氣低頭看著他的腳趾頭。他的腳趾和他的手指一樣細而修長,十隻腳趾的指甲方方的,剪得乾乾淨淨,秀秀氣氣。原來男孩子會像女生,而女孩子可能也會有像男生的地方。我心裡想。
於是我衝動的,傾身向他。然後,浪聲消失了,月光消失了,心跳消失了,我消失了。我像漂浮在真空的氣泡裡,失去聲音,沒有重力。他沒有抗拒。軒永的嘴唇溼潤而柔軟,不像我笨拙又生硬。他的呼吸淺淺暖暖,交換著我的呼吸。
等我的嘴唇離開他的嘴唇後,浪聲與萬獸的鼓譟一起奔回心臟,震得我頭暈目眩。他緊握著我的手,將昏眩的我攬進他薄薄的胸膛。我聽見他的心跳聲,堅定而有力量。
「大浪打來的時候,」他說:「你一定要記得,我從沒有離開過你。」
/
那個晚上之後,我們又回到像小時候那樣,成為彼此的影子。大人取笑我們,只覺得小孩子嘛,中間的空白,只是偶然的彆扭。只有媽媽在軒永幫我夾菜的時候,意味深長地輪流端詳我們兩人的臉。我裝作沒有看見,理直氣壯地將碗伸出去,接下軒永仔仔細細剔完刺的魚。
軒永像以前一樣,帶著我去任何地方,只是從腳踏車換成一台高婆婆騎去買菜的摩托車。在風裡,他斷斷續續地說,剛上國中的那年暑假,他認識了很多人,其中有個男人叫希力頓。對軒永來說,希力頓就是海神之子那般神性的存在,他會衝浪,會潛水,會獵魚,會彈吉他,還造了一艘船。
我第一次遇見希力頓,他剛從海底回來。在陽光的反射下,頭髮溼溼亮亮的,深棕色的肌膚上覆著一層薄薄的鹽粒。可能長年瞇著眼追逐魚,笑起來眼角有深刻的紋路,看起來比他實際的年齡大。但其實,十五歲的我根本不在乎他幾歲,可以是二十五歲,也可以是三十五歲,聽起來都是一個很遙遠的數字。
希力頓非常會料理魚,他笑說大部分的蘭嶼人都很會做菜,因為大家只能念餐飲科。他烤著當天獵來的魚,說魚只要死前有掙扎過就不好吃,一定要一槍斃命。他講的時候還比出手槍的手勢,抵在太陽穴上,嘴巴發出「砰」的一聲。
希力頓常常警告我不要被騙了,用他前任的故事嚇我。他用竹籤戳一戳魚,確認熟度後對著我說:「你以為大海裡最美的一條魚,會是屬於你的。但其實你根本閉上獵人的眼睛。」
「你根本沒有獵人的眼睛。」軒永在旁邊淡淡地說。
「對啦,但我很有耐心,可以在海下待得比別人久。」希力頓遞給我一隻魚,兩面金黃色,鮮嫩欲滴。
軒永轉頭對我說,每個來學衝浪的台北女生都聽過這個故事,然後希力頓會說自己還沒從那段戀情中走出來,但他都是真心的。
「喂,當然要先講清楚遊戲規則啊,懂不懂啊你?」希力頓笑著說。
他從塑膠桶撈起白白粉粉的魚內臟丟向軒永。軒永跳起來閃躲,兩個人在金樽漁港旁,邊跑邊拉長音地笑喊:「你懂不懂──你懂不懂──」
/
那天他們上岸後,希力頓在屋外邊沖洗著裝備邊說,剛剛沒接到電話,村長要他去鄉公所的頂樓做一個木棧板,他得先去市區買些白鐵釘。水聲嘩啦嘩啦,他大聲問我們要不要搭便車回家,裸著上身、防寒衣還溼淋淋地掛在腰間的軒永,看著我回說不用。過一會兒就聽見車鑰匙轉動了數次,才順利發動的引擎聲。
嘴唇發紫的軒永褪下防寒衣扔在地上,衣服躺成一個無精打采的人形。我把大毛巾遞給他,他圍在腰間後脫下溼透的短褲,邊哆嗦邊靠過來。
「你好暖。」
他闔起我正在看的書,將毯子攏在他背上,從身後抱住我。我的背貼著他的胸膛,他溼溼的頭髮貼緊我的臉頰。
(中略)
村長氣沖沖地跑進來,厲聲斥責叫軒永穿上褲子,立刻將我們拎到高婆婆的家屋,要赤裸著上身的軒永跪在廚房的大木桌前。高婆婆緊緊摟著葵,站在庭庭阿姨旁邊。
高婆婆聽著村長激動地描述現場,說是因為希力頓一直沒接電話,便繞過去漁港看看,結果一打開門看到,這不是小馬部落的林軒永嗎?這小子光著身體壓著一個衣著整齊的女生,女生看起來正在哭,手還一直推開他。
媽媽緊緊拉著我的手臂,我拚命想打斷那男人族國語交雜的荒唐描述,準備開口解釋些什麼,但跪著的軒永鐵青著臉,抿著嘴唇看了我一眼,低下了頭。
高婆婆不斷低聲應和著村長,一直說軒永這孩子很乖,他們兩個感情很好,或許只是鬧著玩的。
庭庭阿姨走到媽媽面前,冷冷地問:「是你引誘他的嗎?」
我愣了一下。「引誘是什麼意思?我是自願的。」
「我問是不是你先主動的。」
軒永低著頭說了一句:「聽你在放屁。」
庭庭阿姨轉頭,用恨恨地表情看著軒永。「好啊,既然不是她,那就是你。我就知道你長得跟你爸一樣,個性也一樣,你們最在行的事就是騙女人!」
我永遠記得軒永抬起頭,直直盯著庭庭阿姨說:「我沒有騙她,爸爸也沒有騙你。你不要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你自己是有多誠實?」
一向冷靜的庭庭阿姨被激得滿臉漲紅,瞄了一眼剛進門的父親,突然狠狠甩了我一巴掌。那一掌火辣辣的,打得我眼冒金星,臉朝下地摔在地上。庭庭阿姨用力扳起我的肩膀,揪著領口將我的臉仰高,用盡全力再甩上幾個響亮的耳光。軒永大吼一聲,整個人跳起來要推開庭庭阿姨,卻被我媽媽死命地攔著。媽媽牢牢地擒抱,將她瘦弱的身體掛在軒永的腰間。
父親衝過來將身體擋在我和庭庭阿姨中間,任由她落下發瘋似的拳頭。高婆婆在一團混亂中蹲下身,緊抱著嚎啕大哭的葵,對著庭庭阿姨悲傷地喊:「孩子是無辜的!他們是無辜的啊!」
從沒有被任何人體罰過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疼痛與恥辱。媽媽含著眼淚,什麼也沒有說,緊緊抱我在懷裡。父親連行李也沒有收,上了車就連夜開回台北。我摸著紅腫的雙頰,躺在媽媽腿上大聲而絕望地哭泣,媽媽也無聲地掉著眼淚。她的眼淚和我的眼淚在我滾燙的臉頰上匯流成一條暖暖的小溪,和軒永牽著我的手一樣。
/
回到台北,家裡絕口不提這件事。他們從未親口審問過我,我再也沒有機會解釋真正的原委。我和軒永一樣,緊閉著嘴唇,把頭低了下來。但我知道,媽媽已經不再接起庭庭阿姨打來的電話了。
父親沒收了電腦和手機,請我交出電子信箱的密碼,由他來收發,必要時轉告重要的郵件。取消鋼琴課,取消補習班,取消晚自習,不能去圖書館,放學後和週末都必須待在家裡。如果課業需要上網查資料,只能借用父親書房裡的電腦。
那段日子似乎是父親第一次長時間地待在家裡,他坐在客廳安靜地看著國際新聞,很有耐心地聽我敲打鍵盤。等我用完網路後,他會用抱歉的表情,在我面前確認我剛剛搜尋過的網址。我等同被監禁,很久很久一段時間。
不可能向同學借手機,身為家長會會長的父親早就給導師壓力,說我之前著迷網路,成績落後,學校應該要特別注意。沒有辦法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但在這種昂貴的私立學校,根本沒有人會在意誰發生了什麼事,就算我真的說了,同學應該也不知道要怎麼回應。少女的話題都只圍繞在去國外的哪裡過寒暑假、搶到哪個偶像的限量商品。我只剩下電腦課才能上網,不過也不能直接傳訊息給軒永,也許父親馬上就會看到。而我知道沒有電腦的軒永,手機也被沒收了。
他只能透過那個籃球隊長,阿樹,聯絡我。我們在與阿樹的即時訊息框裡交換訊息。軒永總是一個星期長長的好幾篇,而我只能在短短的時間內盡可能讀完並回覆。那些無力的想念與近況更新,卑微而沒有品質地持續了半年,然後理所當然的,我沒有考上理想的學校。
軒永則意外地申請到最好的高中。這使我覺得公平。他背負了那次所有的罪名,而我承擔之後應得的報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