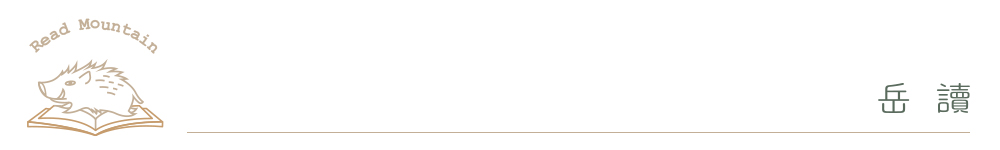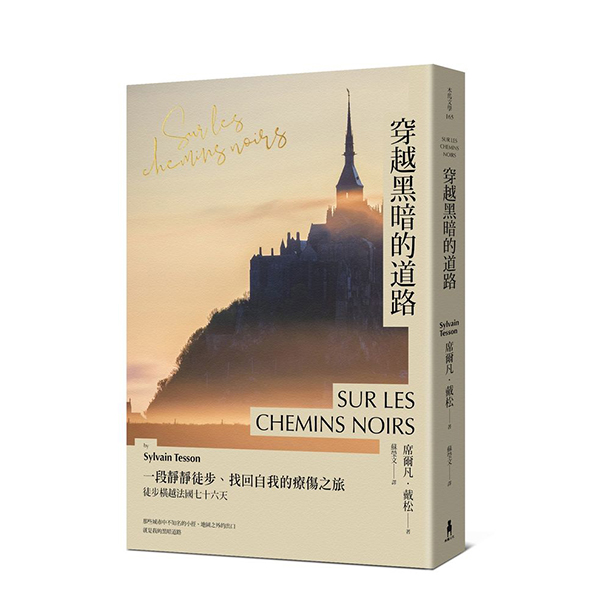那些城市中不知名的小徑、地圖之外的出口
就是我的黑暗道路
從地中海到大西洋
一段走在法國鄉間小路上的美麗復原之旅
「我沒有領土,只能藉由在小徑上步行,成為自己的主宰。」
──排行榜冠軍書《貝加爾湖隱居札記》、《在雪豹峽谷中等待》
法國最受矚目作家,熱賣43萬冊最新中譯作──
同名改編電影2023年在法國好評上映
母親過世後,戴松經歷一場幾乎要奪去生命的嚴重事故後陷入昏迷,當他醒來,發現自己無法完全直立,全身劇痛、一耳失去聽力,身心折磨著他。眼看人生跌落谷底,他決定拖著殘破不堪的身軀橫越法國,從法國最南端一路向北,透過徒步旅行找回原本的自己。
「徒步有兩個好處:治療和遺忘。」
他走進一個個鄉村,穿過廢棄的城鎮與被遺忘的荒野。在古老國度的小路指引下,他感受著孤獨與寂靜,在絢麗的自然風光中吹拂自由的空氣。他仰望法布爾住過的碉堡,遇見僧侶、獵人與牧羊人,在一條又一條黑暗道路上,歷史的鬼魂在他的步伐間穿梭。在粗話、吐槽與烈酒中,他讀書走路,心靈隨腳步變得輕快起來。
「任何長距離行走都帶有救贖的氣息。
而步行帶來我所需要卻難以保有的寶藏:節奏。」
繼暢銷書《貝加爾湖隱居札記》後,戴松再次踏上一場獨特的旅程。他在幽暗的小徑徐徐前行,在旅途中與自我對話。這些從未走過的黑暗道路上,沒有必須履行的責任。這是一場為孤獨與封閉、徒步與自然加冕的復原之旅。他脫離了躁動擁擠的城市,也逃脫了那副困頓痛苦的軀體,最終尋回一度迷失沉淪的自己。
「明天,我不再繼續遊蕩。
我們仍然可以再出發,勇往直前走進自然。
世上仍有充滿日光的山谷,只是沒人能指引你路線;
你可以藉由一個個在壯觀深處度過的夜晚,為那段風中的時光加冕。」
各界好評,靜心推薦
【Tai Tai LIVE WILD】楊世泰 & 戴翊庭──《山知道》、《步知道》、《折返》作者
小歐──四國遍路同好會版主、作家
工頭堅──旅遊產業影響力者、自媒體經營者
李惠貞──獨角獸計畫發起人
連俞涵──演員、作家
黃麗如──酒途旅人
謝哲青──作家、知名節目主持人
戴松在這趟漫遊的旅途中,企圖遠離文明,尋找比帝國更古老的悠遠傳統。這是一次向那些認為該理所當然繼承眼前這個世界的人們,示範轉身拒絕最好的行動。──丹尼爾.霍斯比(Daniel Hornsby),霍普伍德獎(HopwoodAwards)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類雙料得主
一段穿越法國史詩般的旅程,深入各地鄉村回溯帝國歷史。戴松身為知名的探險家和作家,以其優美的文筆引領讀者離開城市,在大自然的美麗中尋找意義。──拉內.維勒斯列夫(Rane Willerslev),人類學家、丹麥國家博物館館長
生動記錄沿路上遇見的人物風景,亦對現代生活進行精采的哲學性批判。──Well-Read Bear Review of Books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在現代生活中尋求內心的豐足,同時探索生活的未知。──Travel Pulse
席爾凡・戴松(Sylvain Tesson)
法國文學家、記者、探險家、旅行家。
1972年生於巴黎。19歲時,騎單車穿越冰島中部、參加婆羅洲洞穴探險,後與好友一同騎單車環遊世界,並將這段歷程寫成《騎行地球》(On a roulé sur la terre)。
之後的旅行經驗包括從尼泊爾到印度的喜馬拉雅山的長途步行,以及騎單車遊歷世界。這些旅行經歷也都成為戴松書籍的主題。
2010年,戴松在貝加爾湖畔居住六個月,其間所寫的日記集結成《貝加爾湖隱居札記》(Dans les forêts de Sibérie)一書,甫出版即銷售破二十萬冊,賣出數十國版權,並榮獲梅迪西文學獎,改編電影於2016年上映。
本書《穿越黑暗的道路》則描述戴松在一次嚴重事故後,從法國南部緩緩徒步到北部的旅程,並重新找回對生活的熱愛。
文字、影像作品四十餘種,遊記、散文隨筆廣受好評。2009年,以短篇小說《和自然一起安眠》(Une vie à coucher dehors)獲頒龔固爾文學獎;同年獲頒法蘭西學院短篇小說獎。2019年以《在雪豹峽谷中等待》(La panthère des neiges)獲頒勒諾多文學獎。
|譯者簡介|
蘇瑩文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外國駐臺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為英、法文自由譯者。近期譯作有《清潔工》、《升級》、《尤比克》、《摯友》、《三股髮辮》、《書海情緣》等數十冊。
|目錄|
前言
一 糟糕的開始
二 廢墟與荊棘
三 黑暗道路
四 暗影
五 朝大海去
|詳細資料|
ISBN:9786263144750
叢書系列:木馬文學
規格:平裝 / 200頁 / 14.8 x 21 x 1.28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前言
這年不好過。長久以來,諸神始終眷顧著我家,我們沉浸在祂們的恩澤中。說不定祂們像童話仙子般照料著我們其中的幾個人吧?接著,微笑轉變成鬼臉。
我們對這些一無所知,自顧自地,漫不經心享用命運賜予的和善。這種隨興使我們忘了最微薄的感激,但也將我們圈禁在讓人筋疲力盡的輕浮中。生活像一幅博納爾的畫。陽光灑在白色的外套上,桌巾上放著水果盤,敞開的窗外,孩子剛穿過果園。戶外的蘋果樹枝窸窣作響:正是痛下重手的絕佳時刻。
重擊很快就來到。我的姊妹、外甥們,全受到中世紀預言中滲入城牆的邪惡所影響:黑影竄入巷弄直奔小鎮中心,抵達城堡的主樓。瘟疫正在蔓延。
我母親的過世,和她在世時一樣讓我們失望。而我呢,我喝多了,爬到屋頂上耍猴戲摔了下來。我在黑夜的邊緣墜落,重砸在地面。要跌斷肋骨、脊椎和頭骨,只需要八公尺的高度。我摔在一身骨頭上。這一摔,讓我懊悔了好久,因為在摔下來以前,這身骨肉還容許我在燠熱的氣溫下過日子。對我來說,有尊嚴的生活就像是西伯利亞貨車的儀表板:所有警示都亮著紅燈,但偌大的車身繼續上路,而預言師以愚蠢的手勢在路上揮舞雙臂,宣告災難結束。整體健康?整體健康導致災難,那八公尺讓我老了五十歲。
我得到很好的照料,回到了人世。就算死去,我也不可能有幸在天上見到我的母親。自從智人演變成現代人類,地球上已經誕生了上千億人。我們真的相信自己能在擠滿小天使的白蟻窩裡找到親近的人?
醫院裡,一切都對我展露出笑容。法國健保制度有極其出色的特點,絕對不會讓你承擔責任。在一個講究倫理的古代社會,人們不會像照顧真正有需要的人那樣照顧醉鬼。沒有人指責我,他們反而拯救了我。最先進的藥物,護理師的照顧,親朋好友的愛,和維庸的詩療癒了我。特別是,有個每天來到我床邊的人滿心聖潔,彷彿我值得動物般的忠誠。窗邊一棵樹將它生氣盎然的喜悅注入了我的內心。四個月後我終於出院,跛腳瘸腿,渾身疼痛,身上流著別人的血,頭骨凹陷,腸胃無力,肺部都是傷,脊椎打了好幾根螺絲,臉孔還變形。生命不再像從前那麼歡樂。
在那些惡夜裡,我立下誓言,該是實踐的時候了。被束縛在病床上時,我幾乎是拉高聲音地對自己說:「要是我過得了這關,我要徒步穿越法國。」我看到自己踏在碎石步徑上!我夢想著露營地,想像自己以流浪者的腳步踏過草地。然而,病房門一開,夢想就破碎了:又是吃果泥的時刻。
一位醫師告訴我:「明年夏天,您可以住進復健中心。」我寧可問跑步機可以帶給我什麼:力量。
隔年夏天來臨,該是我和運氣算帳的時刻。藉由走路、做夢,我要喚醒自己對母親的回憶。倘若我在步道上連續踩踏好幾個月,她的靈魂就會出現。但不是哪條路都可以,我要走的是隱密、圍繞著樹籬,必須披荊斬棘、穿過廢棄村落的小路。只要攤開地圖,只要能夠接受曲折彎拐或得強行通過的路徑,你還是能找到罕有人跡之地。遠離大馬路,你必能找到一個不受喧囂、人工造景及不知名汙染所影響的蓊鬱法國,一片長滿山梨樹,看得見倉鴞的鄉景。醫師們的政治術語是建議我「復健」。自我復健?這得從走向戶外開始。
我可以舉出十來個走入偏鄉的動機。比方說,告訴自己我花了二十年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和智利首府瓦爾帕萊索之間遊歷,當我可以前往國內的安德爾-羅亞爾省時,反而去了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但我將這次避入鄉野的真正原因寫在皺成一團的紙上,放進背包的深處。
一 糟糕的開始
在火車上
高速列車為什麼要保持這個速度?以高速旅行有什麼用?真荒謬,風景以每小時三百公里的速度飛掠,然後我得花好幾個月徒步北上!當速度追著景色跑時,我想著我愛的人,比起表達我的情感,我更善於思念他們。事實上,我寧願思念他們,而不是和他們頻繁往來。明明思念可以讓人們如此接近,這些親朋好友卻老是希望「大家碰個面」,彷彿那是個必須履行的責任。
八月二十四日,義大利邊境
從尼斯搭火車到唐德車站後,今天是我第一天的徒步行程。我踩著虛弱的腳步走向山坳。淡金色的小草隨著晚風擺動,善意展現初見面的姿態,美得無瑕。經過悲慘的幾個月,即使是陽光下的蚊蟲看來也如同好兆頭。在帶著涼意的金黃色光線下,成群飛舞的小蟲彷彿在向孤獨示意;看來宛如字跡。也許它們正在對我們說:「停止你們對自然的全面戰爭」?
路邊矗立著森然的雪松,樹根緊緊攀附住坡地──雪松看似確信自己的位置。一名牧羊人踩著比我穩健的腳步出現在轉彎處,他面容乾枯,宛如紀沃諾筆下的人物。他是在地人。而我呢,我一向是異鄉人。
「你好,你要進城嗎?」我問道。
「沒有。」他說。
「上頭有羊群嗎?」我再問。
「沒有。」
「你下來休息?」
「不是。」
看來,日後我必定得改掉都市人逢人就搭訕的習慣。
唐德的山坳,是梅康圖爾稜線的鞍部,義大利隔著這裡和法國相鄰。我計畫從這裡──法國的東南角──出發,走向科唐坦半島北部。傳統上,俄羅斯人出發旅行前,會在椅子、行李箱或最先入眼的石頭上稍坐幾秒。他們會放空,會想想留在身後的人,擔心是瓦斯是否關了、屍體有沒有藏好──我還知道什麼?於是我像老俄那樣坐下來,背抵著木製小聖壇──聖壇裡的聖母望著義大利的風光冥思。接著,我倏然起身離開。
在山坡上,受損的視力讓我將母牛看成滾下斜坡的大圓石。松木林立的山脊讓我想起從前看過的山,那是二十年前了,襯著藍天,中國雲南的山峰在地平線上畫出鋸齒般的線條。但我連忙將這個想法驅向夕陽。這紊亂的比較會妨礙我的思維。
我難道沒發過誓,要在佩索亞的《異教徒之詩》指揮下度過幾個月嗎:
見植物,我說「是植物」,
見我,我說「是我」。
其他的我不多說。
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喔,我懷疑心神不寧的佩索亞可能從未忠誠對待自己的規畫。你要我怎麼相信這個世界成功地讓他心滿意足?他寫下此等宣言,然後花了一輩子時間背叛自己的理論。在接下來幾星期的徒步旅程中,我要嘗試以不帶任何分析面紗、不經記憶過濾的清透目光來觀察事物。到目前為止,我學會了將自然和眾生當作記錄印象的頁面。現在我迫切要學習的,是不呼喊斯達爾夫人即能召喚陽光,不提及賀德林就能召喚風,不必在杯底看到福斯塔夫也能喝到冰涼的葡萄酒。總之,活得像狗一樣,牠們啜飲和平,吐著舌頭,給人的印象是牠們要吞下藍天、森林、大海甚或落下的夜幕。當然了,此舉必將失敗。你不可能改變歐洲人。
到了海拔兩千公尺處,我在一處水泥碉堡附近看到整片濃密的草地。我生了一堆火。木柴仍然潮溼,我努力吹著小火,吹得我凹陷的腦袋暈眩起來。高溫驅走了大蜘蛛,牠們不再讓我害怕,我看到不少蜘蛛四處逃竄,離開我周遭。黑夜吐出陣陣溼氣,營帳幾乎保護不了我。我感到害怕,這是我從屋頂上跌下後首次在戶外過夜。土地再一次接納我──這回溫和許多。我回到了自己鍾愛的花園:星空下的森林。空氣清涼,地面凹凸不平,地勢是斜坡,一切看似美好。只要我們珍惜戶外的夜晚並且寄予期望,就能將這些覆蓋掉忙碌白日的夜晚高掛在征服清單上。這樣的夜晚免除了上方的遮蓋,釋放了夢想。我聽不見歐洲城市的喧鬧聲,只有空氣!空氣!一年前,在病床上,我做夢也想著要躺在松林下。如今露營時光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