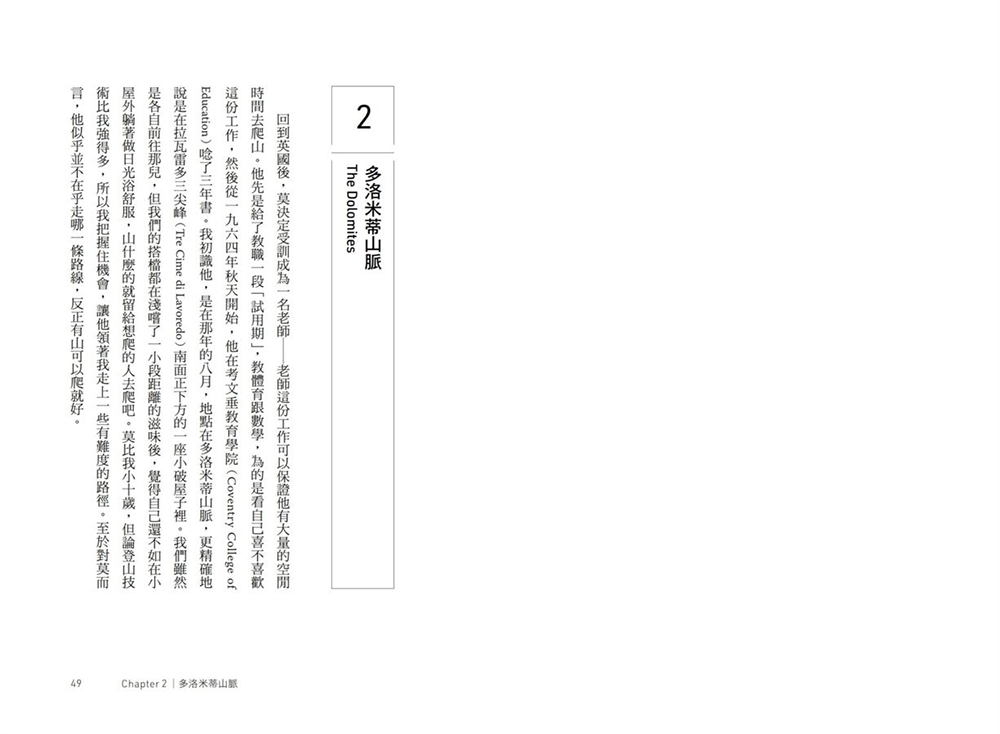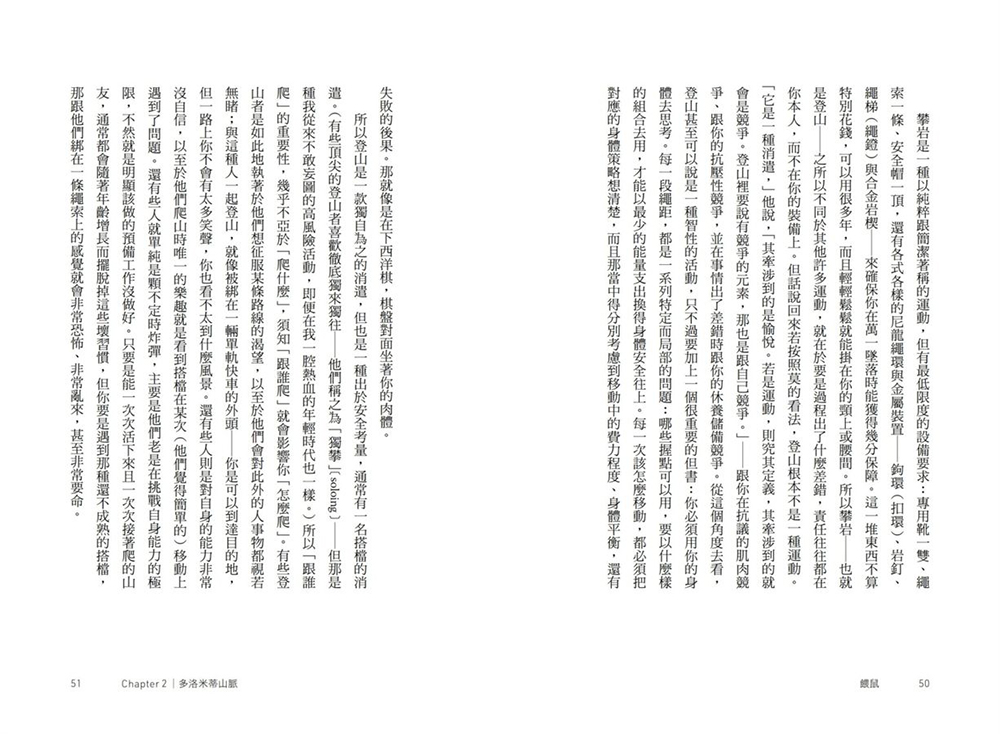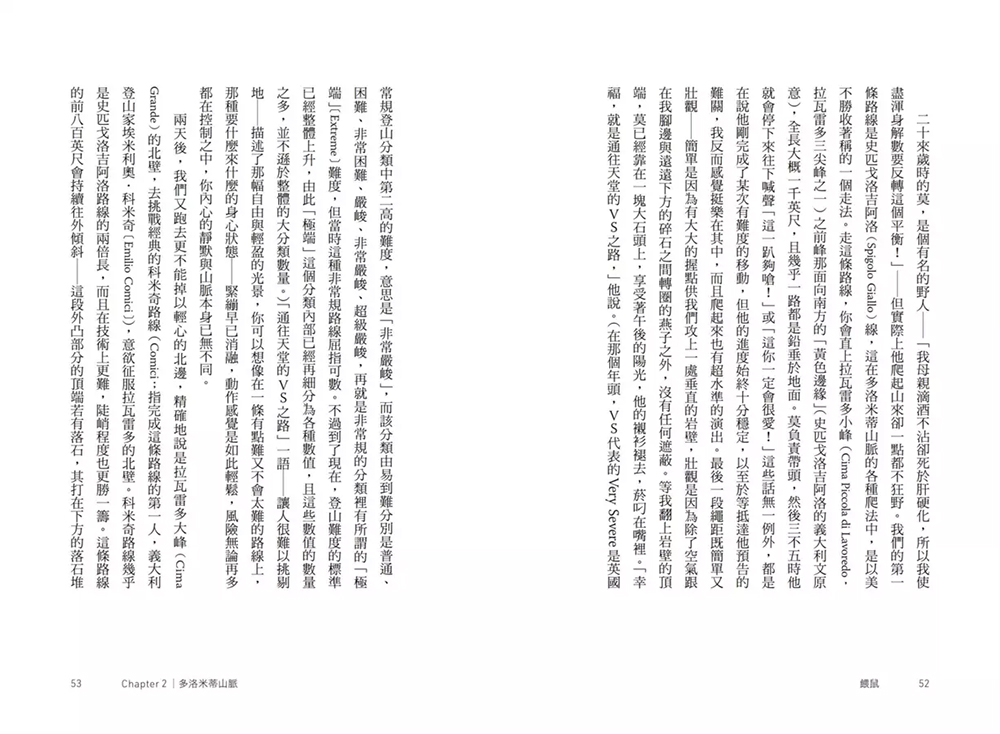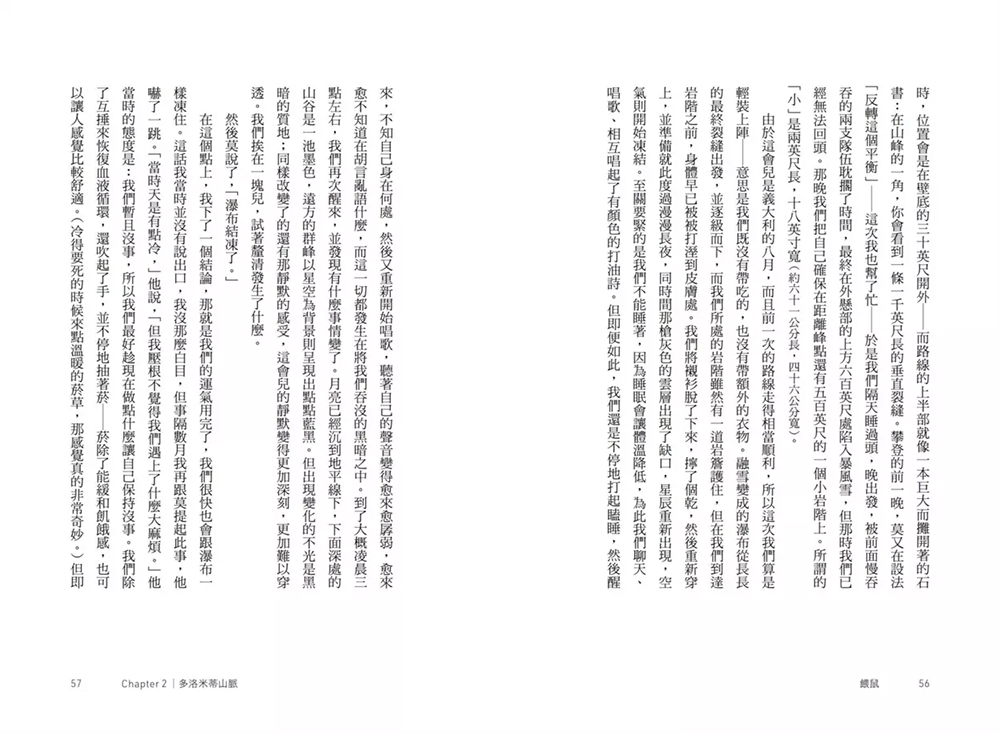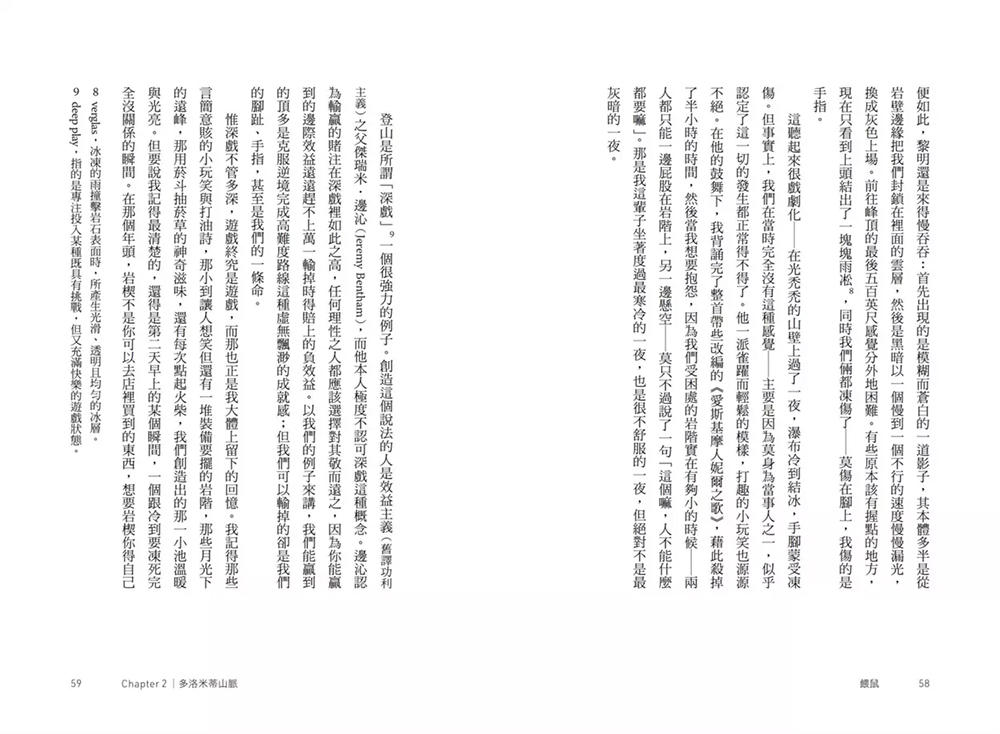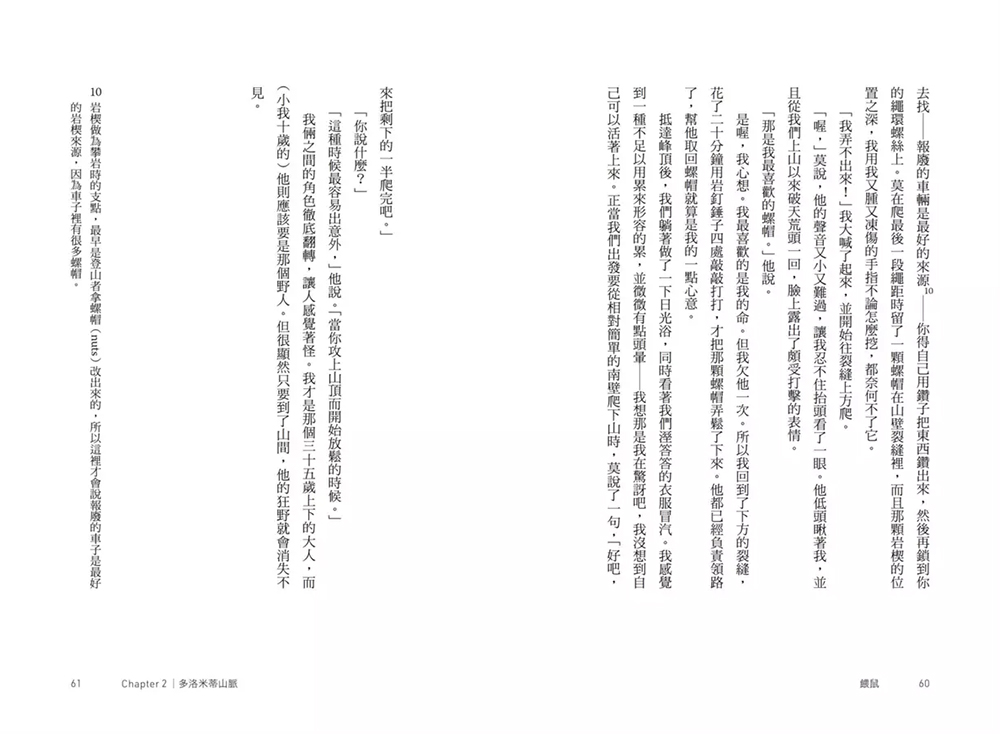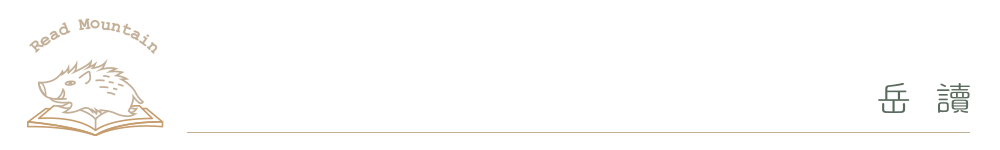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meters山岳文學書系作品|
攀登不為什麼,只為了餵養心中的那一隻老鼠。
登山者心目中的登山者
近代攀登史上的無名英雄──莫.安東尼(Mo Anthoine)
西方登山家傳記經典作,出版35年後中文版首度問世
伍元和 台灣山徑古道協會理事長
江秀真 台灣福爾摩莎山域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呂忠翰 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徐銘謙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資深步道師
張元植 登山家
雪羊視界 山岳作家
──推薦
在西方登山家們口中,「餵鼠」(feed the rat)這句俚語,指的是登山的渴望就像內心有隻無形的老鼠,登山家必須不斷地去餵養牠,因而得要爬上一座座高山,以解這隻鼠的飢渴。而讓這個生動說法廣為流傳的,正是本書主角──英國登山家莫.安東尼(Mo Anthoine, 1939-1989)。
出生於戰亂時代的安東尼,自十九歲起便浪跡天涯,走遍東西方世界,並攀上了各地的山巔。從阿爾卑斯山、義大利的多洛米蒂山脈、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亞、祕魯安地斯山脈,到喜馬拉雅山的八千公尺群峰……在挑戰人類耐力極限的冒險中,安東尼找到了生命中最大的樂趣。這種對挑戰極限的熱情使他成為山岳領域數十次驚險史詩的無名英雄。
英國詩人、文學作家艾爾.艾佛瑞茲,同時也是安東尼的長年繩伴,透過與安東尼的近身觀察、相處與理解,以真摯不矯飾的文筆記錄下這位低調登山奇才的山岳生涯,以及他們之間的深刻友誼,於一九八八年出版成《餵鼠》一書,而隔年安東尼即因腦瘤逝世,享年五十歲。爾後,本書於西方世界多次再版,成為世界登山圈內的一部經典名作,莫.安東尼的生命故事也因此傳頌不墜。在他逝世35年後,此次為首度發行中文版本,讓中文讀者也能看見這位將生命全數奉獻給山的登山家,有著怎樣的心靈與人生際遇。
「沒錯,遠征他媽的很辛苦,你會有害怕的時候,但其主要的部分還是好玩。那當中要是涉入宣傳的考量,那事情就會變成誰想出名,誰就會漠視團隊而一意孤行,所有的事情在登頂面前都可以犧牲。嗯,我真不覺得登頂有什麼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想登頂你永遠可以改天再來。你爬山回來會記得的不是人站在山巔上目空一切,而是在路線中體驗到的點點滴滴。那個過程中最棒的感覺,莫過於你知道你可以倚靠別人,而別人也可以百分之百地倚靠你。」
▍莫.安東尼(Mo Anthoine, 1939-1989)
英國登山家,以其幽默、勇敢和出色的攀登技術著稱。即使生性低調,他在登山界的成就仍使他成為了一位傳奇人物,影響了許多後來的登山愛好者,被譽為「登山者們的登山者」。他不僅在攀登高峰方面有卓越的表現,也因其對登山裝備創新的貢獻而備受推崇。
出生於英國威爾斯的他,年輕時就展現出對冒險的濃厚興趣。他在攀登方面的技術和決心,使他成為了許多重要探險隊的核心成員,包括1977年與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及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等人挑戰「食人魔峰」拜塔布拉克峰(Baintha Brakk)首攀成功。
除了登山,安東尼還創立了自己的登山裝備公司「斯諾登模具」,專注於開發和改進登山裝備,為登山者提供更安全和可靠的工具。他的創新精神和對細節的關注,使他在這一領域贏得了廣泛的尊重和讚譽。
1989年,安東尼因腦癌逝世,享年五十歲,但他的影響力依然深遠,他的故事和成就激勵著新一代的登山者,繼續挑戰極限,探索未知世界。
【各界讚譽】
「登山渴望,如鼠竄動;餵之養之,駕之御之。」《餵鼠》寓意尚不僅於此。野外諸鼠能單打獨鬥,亦能群策群力完成目標;早年登山團體倡導的「夥伴關係」,從本書內容能略窺一二!
──伍元和,台灣山徑古道協會理事長
作者將「登山渴望」形容成「餵鼠」(feed the rat)?想必,挑戰高峰者都具有類似特質!且對此慾望的擴張是自然而然,即使不登山只是在山腳下或基地營靜靜望著那矗立天際的金字塔,內心就已盤算著下回要到更壯麗、更高聳、更驚險的地方。或許會慘不忍睹、再回不來,但他們始終明白:「在山上做喜歡的事做到死,總贏過在醫院的病床上發臭死掉!」
──江秀真,台灣福爾摩莎山域教育教育推廣協會理事長
這本書的名字很快就撬動我,那是一種隱喻,我想的是大自然一直在餵食我們,讓填飽心靈的下一刻就又是起點,不斷尋找更多的能量。好奇心是生命的根,卻會隨著年齡增長與有無勇氣增加探險經驗來延續,然而冒險故事最值得的就是需要自己經歷痛苦及艱難的過程,並親自解決問題的機會與相信自己的可能下,所反饋的內在價值,很像告訴自己又上了一個階梯,運氣好的時候,能踩在死亡的大門前,喊個兩三聲後,讓微笑帶著自己回到人間留下痕跡。我常思考如何給予下一代勇氣與態度,提醒自己少一點焦慮的情緒,能夠吸引他們的是內在的美感,找尋那種對未知事物的毅力果實,也鼓勵考驗自己意志力的火器,漸漸地享受愛上翻岳後的時刻。
──呂忠翰,世界公民兼探險家
我們總是喜歡聽某種「之最」的成功故事,《餵鼠》的主角講述一個登山攀岩領域中平凡而又專業的好手,他沒有把興趣與熱情當成養活自己的職業,也沒有拚命從事其他工作賺錢以便滿足業餘的興趣。餵鼠其實就是內在源源不絕的驅動力,不是為了出名也不連結利益,在技術與經驗上的追求,從事冒險的過程即已完成,不論成功或失敗,簡單純粹。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也能與主角有限的生命共鳴,單純而當下的相遇。
──徐銘謙,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資深步道師
強大而謙遜的莫・安東尼上山追求的並非名聲,而是「在神與人之間」:既能觸碰自己的極限挑戰未知,餵飽心中那隻不斷啃咬自己的老鼠,又能和喜愛的朋友們一同出遊,享受過程的每一刻。在商業利益掛帥、八千米乃至全球高峰幾乎變質為資產階級高級打卡點的當代,又有多少人能像莫一樣享受過程、在乎隊友,乃至於無論遇到多大災難,也從來沒有隊友喪命?
為什麼登山?或許莫的人生,這本世界山岳文學經典,會是一個最樸實、真摯的解答。
──雪羊視界,山岳作家
不論是對那些喜愛登山或攀岩,或者好奇登山家為何而攀,抑或是不愛登山只愛讀書的人,艾爾.艾佛瑞茲的《餵鼠》都將帶給你一次集探險、幽默與絕佳寫作技巧於一書的閱讀饗宴。
──夏偉(Orville Schell),美國知名作家暨記者
──詹偉雄 策畫・選書.導讀──臉譜出版山岳文學書系 meters──
現代人,也是登山的人;或者說——終究會去登山的人。
現代文明創造了城市,但也發掘了一條條的山徑,遠離城市而去。
現代人孤獨而行,直上雲際,在那孤高的山巔,他得以俯仰今昔,穿透人生迷惘。漫長的山徑,創造身體與心靈的無盡對話;危險的海拔,試探著攀行者的身手與決斷;所有的冒險,顛顛簸簸,讓天地與個人成為完滿、整全、雄渾的一體。
「要追逐天使,還是逃離惡魔?登山去吧!」山岳是最立體與抒情的自然,人們置身其中,遠離塵囂,模鑄自我,山上的遭遇一次次更新人生的視野,城市得以收斂爆發之氣,生活則有創造之心。十九世紀以來,現代人因登山而能敬天愛人,因登山而有博雅情懷,因登山而對未知永恆好奇。
離開地面,是永恆的現代性,理當有文學來捕捉人類心靈最躍動的一面。
山岳文學的旨趣,可概分為由淺到深的三層:最基本,對歷程作一完整的報告與紀錄;進一步,能對登山者的內在動機與情感,給予有特色的描繪;最好的境界,則是能在山岳的壯美中沉澱思緒,指出那些深刻影響我們的事事物物——地理、歷史、星辰、神話與冰、雪、風、雲……。
登山文學帶給讀者的最大滿足,是智識、感官與精神的,興奮著去知道與明白事物、渴望企及那極限與極限後的未知世界。
這個書系陸續出版的書,每一本,都期望能帶你離開地面!
▍書系已出版作品──
1 輝耀之山:兩位如風少年的絕壁長征/The Shining Mountain by Peter Boardman
2 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by John Muir
3 攀向自由:波蘭冰峰戰士們的一頁鐵血史詩/Freedom Climbers by Bernadette McDonald
4 靈魂的征途:安娜普納南壁/Annapurna South Face by Chris Bonington
5 攀登的奧義:從馬洛里、尼采到齊美爾的歐洲山岳思想選粹/The Meaning of Mountaineering by Various Authors
6 殘暴之巔:K2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Savage Summit by Jennifer Jordan
7&8 靜謐的榮光:馬洛里、大英帝國與聖母峰之一頁史詩(上/下)/Into the Silence by Wade Davis
9 野蠻競技場:年輕的心與困難的山之最後告白/Savage Arena: K2, Changabang and the North Face of the Eiger by Joe Tasker
10寧為一日猛虎:艾利克斯.麥金泰爾與他的生命之山/One Day As A Tiger: Alex MacIntyre and the Birth of Light and Fast Alpinism by John Porter
▍詹偉雄──策畫.選書.導讀
台大圖書館學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畢業。曾擔任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文創產業創業者,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與《數位時代》、《Shopping Design》、《Soul》、《Gigs》、《短篇小說》等多本雜誌之創辦,著有《美學的經濟》、《球手之美學》、《風格的技術》等書。
退休後領略山岳與荒野之美,生活重心投注於山林走踏與感官意識史研究。2019年協助青年登山家張元植與呂忠翰攻頂世界第二高峰發起「K2 Project 8000 攀登計畫」,目前專職於文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行、寫作。
|作者簡介|
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
艾爾.艾佛瑞茲是一位受到高度評價的英國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與報導文學作家,著有經典作品《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鎮上最大的遊戲》(The Biggest Game in Town,暫譯)等。他的作品長期以來都出現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觀察家報》(The Observer)等刊物上。
|譯者簡介|
鄭煥昇
在翻譯中修行,在故事裡旅行的譯者。賜教信箱:[email protected]。
|目錄|
各界讚譽
登山與現代──meters書系總序│詹偉雄
推薦序──攀登才沒那麼多名堂|張元植
導 讀──你墜落了,你辯證了,你澄明了……│詹偉雄
引言/克林特.威利斯(Clint Willis)
第一章 蘭貝里斯
第二章 多洛米蒂山脈
第三章 史詩
第四章 泉源之屋
第五章 通往羅賴馬山之路
第六章 餵鼠
第七章 愉悅原則
第八章 斯諾登模具公司
第九章 任務
第十章 霍伊島的老人
第十一章 聖母峰
二〇〇一年新版後記
|序|
【推薦序】攀登才沒那麼多名堂
文/張元植
“Feeding the rat”是個流傳於歐美本格攀登者間的諺語,意為出發攀登,滿足內心的騷動與渴望。初次聽到這比喻覺得真是太傳神了,但一直不知這話的出處,更不明其內涵。
閱畢這本小品,掩卷深思。
許多攀登文學或傳記,或有意或無意,都在復刻某種「宏大探險」的敘事。裡頭的角色們普遍具備超人或英雄特質,而他們的經歷,就像在演好萊塢冒險電影。「攀登」,似乎是種展示不俗人生的舞台。
一九七七年,巴基斯坦,海拔七千多公尺令人望而生畏的食人魔峰上。當克里斯.鮑寧頓忍著斷裂肋骨刺進肺部的疼痛,咳著因感染而顏色詭異的濃痰,邊踉蹌垂降求生,尚且不忘這段經歷是回去寫書的絕佳素材。在一旁默默護送下撤的莫.安東尼,也就是《餵鼠》的主人翁,在家鄉媒體事後的報導中,只以「鮑寧頓的快樂夥伴」的形象隱名出現。
不過who cares?他的確就是「快樂夥伴」。
對他而言,攀登才沒那麼多名堂。既非啟迪人心的偉大追求,也不是為了什麼頭銜或紀錄。單純只是餵飽內心那隻騷動的小鼠,是生活中一個找樂子的消遣罷了。就跟每一個平凡人生沒什麼不同。
正因如此,少了公眾目光凝視下的展演,少了名利的算計,攀登高峰,其實就跟「三五好友一同出遊」一樣簡單。人跟人之間也才得以回歸純然的夥伴關係,在惡劣環境中互相扶持。這正是極限攀登中,人性最可貴的品質。
《餵鼠》就是這麼一本關於「登山者心目中的登山者」(climber’s climber)的書。攀登一事,在這樣的攀登者身上,沒有那些冠冕堂皇的辭藻,它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
【導讀】你墜落了,你辯證了,你澄明了……
文/詹偉雄
To snuff it without knowing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are capable of ......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sadder than that.
在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清楚自己能力極限在哪裡的時候就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我想不到還有什麼比這更悲哀的事情。
——莫.安東尼(Mo Anthoine,一九三九~一九八九),英國登山家,引自本書第二一〇頁
Though man lives by habit, what he lives for is thrills and excitement.
The only relief from habits tediousness is periodical excitement.
雖然人類依賴習慣而活,但他們生活的目的是追求刺激和興奮。唯一能緩解習慣帶來的乏味之方法,就是定期的興奮。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八四二~一九一〇),美國十九世紀實用主義哲學家
Within a month of intense life in the mountains is going through so much, what used to be a period of several years; This is an occupancy for people greedy for life - human life is not enough.
在山中度過一個月的緊張生活,經歷的事情相當於以前幾年的時間;這是一種對生活貪婪的人所追求的體驗——人的一生是不夠的。
——亞捷.庫庫奇卡(Jerzy Kukuczka,一九四八~一九八九),波蘭登山家,世界第二位完登十四座八千巨峰者
每本山岳文學,都有一種本領——讓它的讀者徹頭徹尾地了解幾座山,即便這位仁兄或女士僅是躺在沙發上目不轉睛地閱讀而已。這種穿梭於兩者之間的神祕溝通技藝發端自身體,山岳作家的身體召喚他手上的筆,將肌肉與神經記住的遭遇說成故事,讀者的眼球讀了,以虛擬實境的想像力,讓神經與肌肉復原出一定程度的緊張和興奮,於是眼前就是斷崖,伸手就是冰晶,風強雪急,一個踉蹌,就是墜落;當然,讀者是死不了的,但他餘悸猶存,因而心生敬畏。
這本《餵鼠》的核心故事,一樣能讓你記住一座大山——「食人魔峰」(The Ogre),但它之得以成為英美山岳文學的經典之作,表示它的能耐卻又不限於此。確實,如果你把整本書都讀完,記憶中還會有某種難以描繪的倫理學命題的事物,像是金沙或銀粉在鉛字群裡暗暗發光,在此,容我們稱其為「老派登山家」(借用台灣登山思想家伍元和之語)的性靈風範,值得讀者細細思量。
首先,「食人魔峰」在哪裡?
盤踞於中亞和巴基斯坦境內的喀喇崑崙(Karakoram)是世界最高聳的山脈,在它綿延三百英里的範圍裡,平均海拔達到兩萬英尺(六千一百公尺),其中兩萬三千英尺(七千公尺)的山頭超過六十座,而在K2(世界第二高峰,八六六一公尺)的周遭,更是地表兩萬六千英尺(七千九百公尺)以上山峰最密集的區域,比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群更極端。在人類活動史裡,它因地理位置的荒遠而最晚受到探險者的青睞,隨著人類世科技發明、資本累積、冒險技藝的增進,這塊由黑色針尖山頭(在中亞突厥語中,「Kara」是「黑色」之意,而「kurum」是「石頭」的日常用語)織錦的神祕區域,也在二十世紀逐一揭開面紗。但即便高海拔登山的探照燈投向了這裡,許多最高的山峰(例如K2與加舒布魯一號至四號峰[Gasherbrum I~IV])一一地踏上了人類的足印,喀喇崑崙仍有著無數的處女未登峰、大岩壁和新路線,吸引著全世界獨孤求勝的登山者,來此冒險一搏。
一九七七年,《餵鼠》這本傳記書的主人公莫.安東尼(Mo Anthoine)便加入了由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和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發起的一支遠征隊,他們的目標是喀喇崑崙中堅地帶、比亞福(Biafo)冰川的最高點「食人魔峰」,當地語稱拜塔布拉克峰(Baintha Brakk)。魔峰的海拔不是頂尖,只有兩萬四千英尺(七二八五公尺),但它的山體十分陡峭,由南壁直下底部冰河的垂直落差有九千八百英尺(三千公尺),它的山巔與幾座副峰交織,構成一副猙獰的面貌,因而被一八九二年首度來比亞福冰川探勘的馬丁.康威(Martin Conway)男爵命名為「食人魔峰」(後續發現證實康威的發現為冰川旁的第一峰,真正的山系最高峰在其身後,因而此一標高六四二二公尺的山峰被稱為「康威的食人魔峰」[Conway’s Ogre])。在一九七七年之前,有三支隊伍曾對它發起突擊,但都鎩羽而歸。史考特和鮑寧頓在該年的七月首度登上了魔峰峰頂,最後一百米是近乎垂直的岩壁攀登,但他們在下山的過程中遇上了大麻煩,先是史考特在第一段垂降時失足墜落,繩索將他拉住後重重地甩向一道岩溝,兩腳的腳踝都骨折而無法行走,接著是鮑寧頓在另一段下降時重擊摔傷,折斷了兩根肋骨,而且咳出大量黃色的痰,隱約有肺水腫的不妙徵兆。
這一趟遠征眼看著將以不幸告終——有兩名行動出問題的隊員,距離山下的基地營還有三千公尺的高差,要橫渡好幾面的岩壁,又要跋涉長距離的雪原,而且眼前風暴不止,糧食耗盡。但最終的結局能以喜劇收場,多虧的是隊伍中的兩名放棄攻頂的同伴——莫.安東尼和克里夫.羅蘭茲(Clive Rowlands)。他們在前隊攻頂時埋伏在主峰下的雪洞裡,伺機而上,但在聽到史考特失足的慘叫後,便明瞭眼前的任務已完全改變,在接下來的八天時間裡,兩人在激烈的暴風雪中引路前行,從低地營挖出一盎司的甜糖,照顧兩位受傷隊友回到基地營,史考特因無法走路,穿上三條長褲跪著爬行,抵達底部冰川上時雙膝都已血肉模糊。原本在營地留守的隊員以爲他們都已經遇難,先行撤退,莫.安東尼接著走了兩天兩夜的冰河石磧路到達最接近的村落,招集挑夫前往營地,解除了兩名隊友的死亡警報。
當遠征隊回到了英國,首登魔峰的紀錄加上一週史詩般的下山故事,吸引了所有媒體的注意,一時之間道格與克里斯成了風雲人物,但援助他們也失去攻頂機會的安東尼和羅蘭茲卻完全在新聞中占不到一席之地,兩人都不以為意,安東尼甚而更偏愛這種光環之外的自在,但身為好友的本書作者艾爾.艾佛瑞茲(Al Alvarez,一九二九~二〇一九)則不以為然,他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十日出刊的《紐約客》雜誌寫就一篇傳記體長文〈餵鼠〉(Feeding the Rat)——亦即本書(同年出版)的濃縮結晶——試著為老友扳回一些公道,那時莫.安東尼腦瘤復發,年長十歲的艾佛瑞茲顯然想為他留下一些紀錄,讓世人認識這位不在光環內的另類英雄故事。
事實上,艾佛瑞茲的故事一樣有趣,他也是一位登山攀岩的愛好者,如果莫.安東尼的能力是A級——不僅是魔山,還包括川口塔峰(六一八五公尺)首登、加舒布魯四號峰的閃亮大岩壁以及聖母峰無人走過的東北脊(兩者皆功敗垂成),那麼艾佛瑞茲也有C+,足以在英國的文藝中年登山行伍裡鶴立雞群。安東尼靠著開設戶外用品公司、販賣自己開發的岩盔和攀登器材來籌措遠征經費與營生,而牛津大學畢業的艾佛瑞茲則是斜槓型的多工者,他是「英語」研究的權威,曾經到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教書,後來被《觀察者報》(Observer)延攬為詩歌編輯。他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但因為父母親是西班牙血緣的猶太人,因此終身不見容於牛津/劍橋的正港英式學術圈,當然,他也常對學院語多挑釁,嘴中和筆下都不留情面。和窮光蛋身世、好幾年浪跡天涯的莫不同,艾佛瑞茲經營產業的父母為他留下豐厚遺產,一直到他去世(二〇一九年)之前,他的豪宅中始終完備著一整套的僕役與管家,以及無數的藝術收藏。最常造訪他家的晚年摯交是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而被他寫入暢銷書《冒險事業:書籍、撲克、消遣、人物》( Risky Business: Books, Poker, Pastimes, People)之中的極限挑戰者之一是他的鄰居:奧地利鋼琴家阿爾弗雷德.布蘭德爾(Alfred Brendel)。
莫.安東尼與艾爾.艾佛瑞茲都自認自己是「局外人」(outsider),但他們心裡頭應該都清楚,就自身所鍾愛的事物而言,他們的創作應該比絕大多數「局內人」(insider)都高上一大截。莫可以縱情生命於山水,但艾爾是廣義的文化人,他雖然不愛社交,但卻具備強大的鬥性。他創作力驚人,一生寫了二十本書,其中有虛構小說、文化研究和嚴肅的文學批評,讓他聲名鵲起的評論幾乎都是攻擊性的,以證明自己對英國文學的影響力超越高談闊論的圈內人。譬如他於一九六一年編撰的英詩全集《新詩》(The New Poetry, 1962),在導言中,艾佛瑞茲是這麼開場:「倫敦老男孩圈子可以是愚蠢的、寄生的和自負的」(The London old boys’ circuit can be stupid, parasitic and conceited),「這本書為我招來更多敵人,但這是我故意的,這是一種對他們的不屑一顧(it was a kind of fuck them)」。身為編輯者,艾爾心裡可是有一套牢固的倫理學標竿的,於他而言,藝術不是十九世紀古典詩人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那般平靜的作品,而是痛苦、憤怒和自我毀滅的白熱化產物,因而在這本詩選集裡,他貶抑當時主流的田園風哈代學派,反倒頌揚泰德.休斯(Ted Hughes)這位冷門詩人,最後甚至捲入了休斯與美籍女詩人妻子西爾維亞 .普拉斯(Sylvia Plath)的痛苦婚姻關係之中。
莫.安東尼與艾爾.艾佛瑞茲的另一個生命共同點,是他們都認為生命的依據並不是先驗的、追尋的,而是遭遇的、生成的(being as becoming),在人還沒有起身去過生命之前,人生其實是不存在的,因此,冒險就成了兩人生命史裡面共同的主旋律,成為不可或缺的心靈深戲(deep play)。兩人的首度相識,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兩人相偕攀登義大利北方阿爾卑斯多洛米蒂山區,受風雪襲擊受困在一個高處懸岩上,必須度過寒冷的一晚(本書第二章),當時感受到寒氣刺入骨髓的艾爾以為自己死定了,而小他十歲的莫卻老神在在,帶著作者跨過人生邊界;讓艾爾刻骨銘心的另一趟,則是讓莫帶他重新去爬一處艱難的岩場「霍伊島的老人」(The Old Man of Hoy)(本書第十章),這時艾佛瑞茲已經五十六歲,準備高掛登山鞋了,沒想到這一趟攀登,作者心中的那隻老鼠胃口又被養大了,他看著年紀小他十歲的莫如此輕鬆寫意,內心百感交集,沒想到不過四年,莫便撒手人寰了。
艾佛瑞茲的一生都在跟「意義感」這個概念搏鬥,他在年輕時非常崇拜小說家勞倫斯(D. H. Lawrence),以至於在二十七歲時與宗師的遺孀弗雷妲.勞倫斯( Frieda Lawrence)之孫女烏蘇拉.巴爾(Ursula Barr)結婚,一心以為如此便與小說家建立了隱性的師徒關係,沒想到這場婚姻是場悲劇,艾爾數度想自殺,五年後以離婚收場。一九六三年,好友女詩人普拉斯因憂鬱症自殺,艾佛瑞茲將她的故事與自身經歷寫成《野蠻的上帝》(The Savage God, 1971)一書,是研究現代自殺行為的先驅之作。而他總結自身失敗的婚姻,也寫出另一本暢銷書《婚姻之後》(Life After Marriage, 1982)。他也寫撲克牌賭博而成另一本經典的拉斯維加斯研究《城中最大遊戲》(The Biggest Game in Town, 1983),能寫出這報導文學的背景,當然也因他真的是一位箇中好手。當他在一九八八年出版《餵鼠》之時,艾爾已經是有名望的大作家,《紐約客》也前所未有的給了他二十六頁篇幅,讓莫.安東尼獲得了隆重的注目禮,他確實做到了他做為文化圈反骨的自我期許:成為一位讓菁英、大眾與自己都備感意外、又深深期待的艾爾.艾佛瑞茲。
「餵鼠」這個詞彙則是莫.安東尼的發明,艾爾用這個生動的意象做為莫.安東尼傳記的標題,顯然他也是折服的。莫不像艾爾讀過大小文學經典,但他是一個直面生活真相的人,他感覺到自己身體內有一個分身,三不五時地對理性的大腦呼喊:找一些危險來餵我吧!對莫而言,「餵鼠」是一種給自己的年度健康檢查,生命過得有沒有意義,不是完成了多少社會與大眾期待你的任務,而是自己有沒有來到生死界線,魂魄有無放大,內心的那頭老鼠或蠻人,有沒有得到滿足。
光從字面上看來,讀者很容易就會認為莫.安東尼是一個極其魯莽之人,但細讀這本書你卻會發現實情正好相反:為了餵飽心中那頭老鼠,冒險者要為冒險做好各種準備,而且在過程中嚴守紀律,「那就像是在下西洋棋,棋盤對面坐著你的肉體」。在他短暫的五十載人生中,與莫.安東尼一齊爬山、冒險的隊友從沒發生過致命事故,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絕口不吹噓自己的事功,這在上世紀八○年代開啟的大山競逐紀元年代裡,無疑地是老派得不能再老派的一種風範。
反倒是——在朋友眼中——艾爾.艾佛瑞茲的武勇之心,比起莫來莽撞許多。除了登山之外,他喜歡打撲克、開快車,在六○年代他帶隊攀岩之時,一位老隊友麥克諾特.戴維斯(Ian MacNaught-Davis)說這位隊長很喜歡「墜落」(falling),讓自己被繩子拉住後彈起來嚇隊友們一跳。艾爾也超愛面對挑戰,大學時著迷拳擊和橄欖球,看過他照片的人都難忘記他的面容,有一顆高聳的額頭和山脊轉彎的鼻子,那便是在一場青年拳賽中挨上一記重拳的結果。他曾經對後來撰寫他訃聞的作者說過:攀登是另一種形而上的拳擊(pugilism),一場面對面的決鬥(a duel)。當然,你也可以說,艾爾面對的山和岩壁,比莫所面對的小兒科太多了,相對安穩的生活足以支持他這種激進的生活態度,但如果我們站在艾爾的角度設想,他的主要人生場域是唇槍舌劍、冷嘲熱諷的文化圈與文學界,如果沒有一點點粗野和狂放,他如何安頓抑鬱不安的靈魂?對他來說,攀登何嘗不是一種對社會的小規模、玩世不恭的反叛,所以當他遇見無政府、反文化、原始赤裸的莫.安東尼之時,會如此地一見如故。莫在年輕歲月作過環遊世界的大夢,為了待在澳洲,他進了一家石棉工廠打工,為了爬巴基斯坦大山,他走私綠松石籌措旅費,在艾爾的眼中,莫的人生知識不是從書本而來,是從人與萬物的交往而來,當讀者讀完這本《餵鼠》甚至會有一種感受:夙有「博學作者」稱號的艾爾真心地認為——莫才是他心中道地的博學者。
《餵鼠》出版迄今已經三十六年,主角和作者都已不在人世,除了山脈和巨峰仍然屹立在地圖的那些角落,世界登山社群的價值倫理也經過天翻地覆的熱議:收集未登峰、處女航跡、競逐年度金冰斧獎,到底是對自己有意義,還是透過「對別人證明」自己更有意義?攀登山岳開著網路直播,經營網紅社群聚攏人氣,與十九世紀初來乍到喀喇崑崙探勘者的純淨心思相比,收穫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
透過兩位登山者的忘年交誼,莫與艾爾不約而同地揭櫫了他們心中的倫理學面向——生活裡,那些是善,而這些是惡;這些道德判斷交織在《餵鼠》的攀登故事中,不止牽動他們的運動行止,而且構建了他們有況味的人生。在這失去準繩的年代裡,這本書提供的是一種有冷冽、清新空氣的閱讀,足以讓海島的腦袋與思維澄明——我是這麼認為!
|詳細資料|
ISBN:9786263155107
叢書系列:Meters
規格:平裝 / 224頁 / 18.8 x 12.8 x 1.5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出版地:台灣
適讀年齡:0歲~99歲
|內容連載|
▍第六章 餵鼠(節錄)
莫對於推動著他──乃至於推動著大部分登山者──去自虐的那股動力,有一個很生動而準確的表達法;他稱之為「餵鼠」。他從羅賴馬山回來後,他心中的老鼠被餵得飽飽的,但我眼中的他卻從來沒有這麼消瘦跟這麼憔悴過。但即便如此,他還是沒隔幾個月就又開始盤算著要再來一次遠征,只不過這一次潔姬說什麼也不肯被晾在家裡,於是他們決定找三個朋友──比爾.巴克(Bill Barker)、馬爾坎.豪爾斯(Malcolm Howells)、伊恩.坎貝爾(Ian Campbell)──搞一趟私人行程,目的地是浪塘喜馬拉雅這塊在聖母峰以西,且大約十二英里外就有希夏邦馬峰的區域,其中希夏邦馬峰是唯一一座完全處於中國境內的八千公尺高峰。為了省錢,他們從威爾斯開車走陸路取道阿富汗,到了加德滿都。他們只拿到縱走而非大規模遠征的許可,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按莫的說法──「敲掉一點岩柱,爬上一座小山峰──大概兩萬一(千英尺)吧,好像是。是挺辛苦的,走起來距離不短,但那感覺很好。」巴克、豪爾斯與坎貝爾先成功登頂,莫與潔姬隨後跟上,只不過兩人對於他們在高海拔上會有什麼表現,兩人都有一點緊張,雖然莫其實在托羅山有過上到兩萬英尺的經驗。事實證明「潔姬像輛小火車健步如飛」,而莫這邊感覺問題也不大。
那年是一九七四,從那之後到一九八三年的每個夏天,莫都會重返這些世界之巔等級的山脈,不是去喜馬拉雅就是去喀喇崑崙。大部分這類遠征都頗為低調,資金大部分是由山友自掏腰包──偶爾才會有聖母峰基金會(Mount Everest Foundation)與英國登山委員會(British Mountaineering Council)幫一點點忙──不會有一般媒體報導就算了,甚至連圈內刊物如《山岳》(Mountain)或《高處與登山者》(High and Climber)也都隻字不提,除非是他們登上了山頂。這些行程與其說是一般大眾想像中的遠征,不如說是莫與他的快樂夥伴們去踏青的完美一天,只不過踏得遠了一點、高了一點。
唯一的例外發生在一九七七年,當時莫獲邀加入挑戰食人魔峰的團隊。食人魔峰就是喀喇崑崙山脈的拜塔布拉克峰,海拔兩萬四千英尺,為比亞福(Biafo)冰川區的最高點。那條路線既長,又對技術要求甚高──途中得克服花崗岩與結冰的陡坡,那些關卡即便是搬到只有一半高的阿爾卑斯山,也一樣難爬──近六年來已經有兩支英國隊跟兩支日本隊在這裡鎩羽而歸。換句話說,這裡絕對可以把老鼠餵得飽飽的。
雖然莫認識另外五名隊員,而且也都算喜歡他們,但五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克里夫.羅蘭茲(Clive Rowlands)──跟他算熟,而且只有兩個人──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與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是全職的專業登山者。唯一一個有名到連徹底的圈外人都認識的,大概就是鮑寧頓了:他寫過好幾本書,還主辦過好幾趟廣獲報導的高山遠征去挑戰像聖母峰與安娜普納峰這樣知名的高峰;他已經是固定的電視咖,各式與登山無關的產品報紙廣告上都看得到他代言的臉龐。史考特做為一個鬍子大力氣更大的彪形大漢,既沒那麼有名,也完全不屬於體制內──這說的是政治體制,他自承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他創下過許多傲人的首登,而且他的資金都是靠巡迴演講賺來。每個登山者──職業也好業餘也罷──都想要在所處的路線上登頂,再小的路線也一樣;登頂就是登山這場遊戲的目的。然而對於專業登山者而言,巔峰會散發一種業餘山友所不太能體會、特殊而切身的強烈感受:那簡單講,就是專業登山者的本質。在食人魔峰之上,他們狠狠地補充了他們的本質,雖然巔峰本身只是山的一小部分。
到了要最後衝刺的時刻,初始的隊員已經從六名變成四名:保羅.「圖特」.布雷斯威特(Paul “Tut” Braithwaite)已經因為落石而負傷;尼克.艾斯考特(Nick Estcourt)因為一開始跟鮑寧頓組隊攻頂施力而氣力放盡。所以此刻只剩下史考特、鮑寧頓、克里夫.羅蘭茲與莫在山上,另外兩人就在底下的冰河基地營裡等著。
食人魔峰有兩處峰頂,分別是西峰與主峰──其中主峰高出兩百英尺──由一道鋸齒狀的長長山脊連在一起。七月十二日,莫與羅蘭茲領頭登上了西峰,然後這四名登山者在東南壁上挖了一個冰穴過夜,位置就在鋸齒山脊的下面一點。隔天早上,史考特與鮑寧頓沿著山脊下方移動,開始攀爬主峰塔下面那些險峻而困難的岩層。由於莫要負責替BBC拍攝攀爬的過程,所以他們的計畫是讓他與羅蘭茲在冰穴裡等一小時,期間兩人會拍照並保持體溫,之後再跟隨其他人登頂。但等兩人按計畫來到主峰塔的基底時,他們發現鮑寧頓在一心想登頂的狂熱中,忘了把裝備留在原地給他們用,而莫與羅蘭茲也沒有攜帶備用的裝備。不過儘管如此,莫羅兩人還是設法以自由攀登(裝備只能用來確保安全而不能用來協助前進)的方式,前進了兩段困難的繩距,來到了他們能用喊聲與另外兩人溝通的距離。此時,史考特已經來到一片峭壁頂端光禿的岩面上,並且正準備要以鐘擺法擺盪到側邊的一道裂縫處來獲致比較容易的登頂路線。(鐘擺法是一種在找不到握點的山壁上進行橫渡的技巧。登山者會把繩索盡可能固定在他能搆到的最高點,然後把身體放低並像鐘擺一樣前後擺盪。此時的登山者會貨真價實地在山壁上助跑,並藉此蓄積足夠的動能去抵達另一條地理學所謂的弱線〔line of weakness〕上。鐘擺技巧在像優勝美地這類地方進行硬石攀岩的時候,不時會派上用場──像要在著名的酋長岩〔El Capitan〕上克服外號「鼻子」的岩塊,就需要用上一種獨特的高難度鐘擺──但在高海拔用上鐘擺還是挺罕見的。)鮑寧頓往下喊聲說這是最後一處必須認真攻克的繩距了,而等他們前兩個人上去後,他們會把繩索垂下去給另外兩個人。惟此時只剩兩個小時就要天黑了,所以莫與羅蘭茲非常不情願地下了一個決定,他們要撤回到冰穴裡,隔天再自行攻頂。
史考特與鮑寧頓順利登頂,拍好了該拍的照片,然後展開了回程。等到他們退到之前擺盪處的頂端時,天已經幾乎全黑了。史考特垂降了下去,穩穩地把自己一推,為的是將自己推過岩壁,返回先前做為擺盪起點的岩釘。
後來在一篇刊載於《山岳》雜誌的文章裡,他描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把身體往前傾,好把自己固定在一顆營釘上,同時想用腳把自己推過去。為此我伸出了右腳,靠在了岩壁上,但在愈來愈黑的夜色中,我不小心把腳放到了薄薄的水冰表面上。突然間我的腳一滑,然後我就發現自己盪進了暗夜中,只能用手抓著繩頭。我想像不出為什麼自己會這麼盪個不停。我沒意識到自己垂降的地方太偏左邊了。我從頭到尾一邊盪,一邊發出混雜了驚嘆、訝異與恐懼的叫聲,而且聲音大到莫從兩千英尺下的雪穴裡都聽得到。最後擺盪與驚呼同時告一段落,是因為我狠狠撞進了山溝的另外一頭。」
這次衝擊讓他左右腳踝都斷了。鮑寧頓垂降到了他的身邊。但這時天色已經全黑。他們一起繼續垂降,來到了一大片雪地中──史考特垂降時是讓背貼著岩壁,至於走路則只能跪著用膝蓋走──然後就咬著牙在那兒野營。
莫與羅蘭茲從冰穴處目睹了意外的發生,為此他們十分震驚,但也知道在黑夜裡他們無能為力。天一亮,莫把羅蘭茲留在洞穴裡,讓他先把茶泡好,自己則出發去救人。還是只能跪著的史考特看到他,開心地說了一句,「你來幹嘛,我一下子就能回到雪洞了,年輕人。」然後他又感覺挺認真地問了句,「你跟克里夫要攻頂嗎?」
莫的回答其實有點長,但其中可以印出來的部分是:「我想我們在這兒可能有些工作要做。」
主要的問題是他們距離下方的基地營,垂直距離有九千英尺(約二七四三公尺),而且實際走起來大部分路線都是彎彎曲曲的。史考特想往下垂降的問題相對不大,而且靠著他過人的力量,史考特也可以把自己往上拉。但跪著走路──就算是下坡──都既困難又疼痛。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次要的問題:即便他們決定立刻掉頭下山,他們也已經在攻頂的前一晚就幾乎耗盡了存糧。
回到冰穴後,他們判斷因為剩下的登山器材已經不多,所以他們最安全的下山路徑應該是先爬回到西峰的頂端,然後再從那裡下山,因為從西峰頂端下山,大部分的路程都會是下坡,只不過這些下坡很多地方是要用走的。在這之前,起碼天氣都相當完美。但等他們做成了上述的規畫後,雲層便開始湧入──「雲好像真的很愛這樣落井下石,」莫說──甚至到了午後偏晚,天上還開始下起了暴雪。他們終究耗盡了儲糧,然後為了把入口擋住不讓雪飄進來,而度過了一個頗為煎熬的夜晚。
暴風雪隔天吹了一整日。上午十點,羅蘭茲帶上繩索去嘗試硬闖西峰。結果他花了一個半小時,只前進了五十英尺;回到洞穴時的他衣服上結了層冰,手也已經完全沒了知覺。一個小時後換莫去試試身手。羅蘭茲稍早明明在及腰的粉雪中開了條路,但現在已經什麼痕跡都不剩了。莫只在一片白茫茫中前進了三十英尺,然後就放棄了。他同樣搞到手完全沒了知覺;事實上外頭冷到他的睫毛都凍到眼睛上了。之後他們就這樣在洞穴裡待了一整天,除了聽著外頭的暴風雪大作,就是拚了命保持入口處的暢通。
暴風一直吹到了隔天早上,風勢確實有稍微放緩,只不過不管天候狀況如何,他們都不能再繼續在洞裡待著了:他們的食物已經耗盡,用來融雪當飲用水的瓦斯罐也只剩下一只,同時他們知道在那樣的高度與狀況下,他們很快就會虛弱到動彈不得。羅蘭茲率先出發,緩緩地踢起了深度既深角度又陡的粉雪;然後是史考特一邊跪著,一邊用上升器把自己往繩索上拉動;莫就像牧羊犬一樣,跟在他們身後,而鮑寧頓則留在冰穴中直到最後一刻,免得他們一個不小心又得撤退。在通往西峰那最為陡峭的最後一段路中,粉雪深到即使是力大無窮的史考特都覺得他只是愈走愈下面。所以莫就爬到前面去幫著羅蘭茲拉,而鮑寧頓則殿後並負責推。就這樣一前一後,一拉一推,中間的史考特也上到了西峰頂端。
後來我問過莫,我想知道他有沒有想過他們可能沒辦法活著下山,畢竟暴風雪是真的很大,而史考特的傷勢也真的不容小覷。對此他的回答是:「我壓根沒想過我們可能會死在山上。當然我知道要是我們一直留在洞裡什麼也不做,那毫無疑問地,就是坐以待斃,因為沒有人會上山營救我們。但我的想法是,只要我們持續往前走,就一定能存活。我們是四名硬漢,而且我們運氣還很好,因為我們受傷的正好是那個硬漢中的硬漢。要是弄斷腳踝的不是像道格這樣充滿力量的鐵漢,那事情或許真的會有不同的發展。但道格本身對受傷一事處之泰然,即便身在痛苦之中也沒有一句怨嘆。我們事後聊起這件事,他告訴我他心裡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會葬身在山間,一點也不。他說他既信得過自已的夥伴,也覺得自己足夠強壯。」
在後續的描述中,史考特寫道:「面對那樣一個龐大而繁複的問題,我唯一能去處理的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一天把一天過好。讓『我一定得回到基地營』的大信念縈繞在心間,但每天醒來別想太多,只要想著怎麼完成這天的目標就好;只要相信若每天的攀登都能確實完成,整個問題終究能獲得解決。」
他們全員上到西峰,已經是中午了。風暴仍在呼嘯著,但能見度已經改善到五十碼,而且最起碼他們已經不用與垂直的上坡奮戰。由於莫與羅蘭茲身上沒有傷勢,同時也不曾因為在食物與裝備雙缺下被迫在兩萬三千五百英尺處野營,所以他們的身體狀態比另外兩人明顯好上一截。也正因為如此,莫從此處接手了領頭的工作,負責找路線,固定確保,還有搞定垂降;羅蘭茲待在史考特身邊協助他通過一些困難的地方;而鮑寧頓則負責殿後。那天,他們的目標是抵達第二處冰穴,位置在西峰下面大約一千英尺處。朝其垂降倒不是什麼大問題,但垂降完要通往洞穴有一段既長且難的陡峭冰面,那才是他擔心的部分:因為那是一段橫向的路程,所以他不可能不帶隊穿過去,而在那種很糟糕的狀況下,那意味著他們有可能掉下去。「幸運的是我在垂降的過程中都一直被這件心事折磨著,」他說。「以至於等冰面前出現在我面前,緊繃到不行的心情反而讓我吹著口哨就穿過了那裡。恐懼與腎上腺素的威力真的很神奇!」
在第二冰穴的那一夜,過得就跟其他的每一夜一樣慘。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給彼此的腳按摩,不然就是相互把腳放在搖籃一樣的大腿上,就盼著這樣可以恢復血液循環。時間來到隔天早上,暴風雪還是未顯頹勢。他們下方是一根上千英尺的石柱──那是他們爬上來時最困難的部分──再往下則是三號營:兩頂小帳篷,同時他們希望裡面能有一些食物。所以他們決定頂著暴風雪與零度以下的低溫動身,即便這一整天他們都只能一直垂降,且在到達三號營的帳篷前都不會有地方提供遮蔽。向下移動到半途,負責殿後的鮑寧頓從垂降的繩索尾端噴了出去,撞擊到下方的一顆巨石,弄斷了兩根肋骨,其中一根還傷及他的肺部。「寒冷的天氣還在繼續變冷,所以他沒有選擇,只能繼續下山,」史考特寫道。「老天保佑,他並沒有馬上開始體驗到後來讓他很不舒服的胸痛。搭起帳篷的他們,看上去就是個可憐兮兮的小隊。第一個到的莫得設法把帳篷重新立起來,因為兩頂帳篷都已經在三英尺的積雪下被壓扁了。」
三號營並沒有吃的,但有茶包、燃料,還有最重要的,有一包一磅重的糖。所以等他們在意外後的第五天早上醒來,發現一個晚上又下了兩英尺的雪,而且暴風雪肆虐得比之前還厲害了之後,他們決定在原地再等一天,看風雪會不會過去,期間他們希望甜甜的熱飲可以幫助他們恢復一點活力。
鮑寧頓的狀態有點慘,咳個不停以外還吐著看起來顏色很不對勁的痰。他的狀況一天天愈來愈差,而且他愈來愈確信自己的喉嚨痛與肋骨下方的痛,是出於肺水腫──那是高海拔登山者的職業病。若果真如此,那他唯一的生路就是盡快下山就醫,否則情況就會非常危急。隊友們聽著他的咳嗽與哮喘聲,心裡憂心忡忡,但還是為了讓他心情好點而說他們聽不到那應該就是肺水腫的咕嚕聲。鮑寧頓完全笑不出來。
在緊急狀況下,莫習慣勉強自己,同時讓隊友們的怪癖可以有很大的迴旋空間。他有著一雙慧黠而睿智的眼睛,但這雙銳利的眼睛並不是用來占別人的便宜。那都只是他遠征哲學的一部分,亦即對他而言,跟一群好傢伙同行重如泰山,登不登頂輕如鴻毛。事後他用非常能同理的口吻,向我描述了鮑寧頓當時的困境:「克里斯知道他弄傷了自己,但他不曉得傷到了哪裡。他只知道自己的狀況惡化得很快。他還知道要是胸腔在高山上出現感染會造成什麼結果,沒人說得準,主要是高海拔會讓病情變複雜且發展速度變快,由此你的身體狀態會在極短的時間內急轉直下。道格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兒:他弄斷了左右腳踝。但克里斯完全在狀況外。你對自己體內的無名未爆彈提心吊膽,對精神面絕對不是什麼好消息。就這點而言,我對他感到十分不捨。但是在生死交關的處境下,人會變得有點冷血。那傢伙就躺在你旁邊的睡袋裡,你可以聽見他在那裡『啊啊啊……啊啊啊。』那自然是糟糕透了。但你的身分不是加護病房的護士。所以你不會說『乖,不痛不痛』,你會說『振作一點──你有該做的事情要做』。」